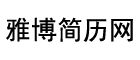诺贝特·埃利亚斯的个人简介
诺贝特·埃利亚斯,犹太裔社会学家,1898年出生于德国里斯劳(即现在波兰的弗劳茨瓦夫),199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去世。家庭背景
他于出生于原属德国、战后划归波兰的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海尔曼·埃利亚斯是位富商,并拥有一爿专为大户人家制作西服的工厂,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退出工商界赋闲家居。退休后他依然受人尊敬,在税务局担任荣誉性的职务,为此他对其一生颇有一种成就感。母亲名为索菲,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有关家庭财政的事她全由夫君做主,自己维持着一个活跃的社交圈子。
生平经历
上学时期聘请一位“小姐”担任家庭女教师,乃为当时的风气,埃利亚斯家也未能免俗。不过父亲经常调换人选,这使得孩提时代的他疲于应付。诺贝特自小身体孱弱,儿科中几乎所有的病症都光顾过他,为此家人没送他去幼稚园,另聘一位男性教师为他进行三年的学前教育。1903年,他进入约翰内斯文理中学的附属小学。该校小学生一律穿校服,戴校帽,用铅笔书写,一般的学校则没有如此的气派,用来写字的是石板石笔。当时德国有三大犹太人聚居的城市,首推柏林,次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名列第三的则是布雷斯劳。约翰内斯文理中学犹太学生特别多,犹太教师也多。犹太教师中有几个是市议员,隶属自由党,这对校风也产生了某种影响。 体质柔弱的埃利亚斯在约翰内斯文理中学如鱼得水,学业名列上等。那时是按成绩排座次的: 学习差的座位在前。据其同学回忆,诺贝特总是在后面排排坐,尽管他身材矮小。学校犹太人虽多,但犹太教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几个拉比讲授宗教课,也只是应景而已。埃利亚斯在其回忆中津津乐道的乃是该校的普鲁士人文主义传统对他的影响,几位杰出的教师所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埃利亚斯特别喜欢钻研哲学,在高年级,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哲学兴趣小组,主要阅读以艰深著称的康德的著作,并在阅读速度和理解深度方面展开竞赛。埃利亚斯如此“自讨苦吃”,是因为他早就下定决心要在满布荆棘的文人学者之路上跋涉,有意识地进行一番智力上的磨炼。对哲学的迷醉,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崇敬,对以席勒和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的热爱,这一切都为其名山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国的排犹、反犹并非自希特勒始,然而在威廉皇帝治下的德国,犹太人在法律上还是受到保护的,经济上也有着平等竞争的机会。埃利亚斯家道殷实,属于中上层,和那些沿街叫卖、衣衫褴褛、满口葱蒜味的“犹太佬”相距遥远;埃氏一家虽则皈依犹太教,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可他们德国公民的自我感觉更加强烈。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偶尔发生的仇犹事件,并没有使他们受到真正的伤害;在他们看来,这仅仅是没有教养者的幼稚行为,不值得跟其一般见识。正如埃利亚斯在其生平漫笔中所写的,他们过的是一种“人身、经济和文化受到保障的生活”。康德的理性批判精神,歌德的世界公民的胸襟,都为犹太人融合整合于德意志社会开启了方便之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擂响之后,德国犹太人也纷纷走向战场,为德意志帝国流血牺牲,不少人战功卓著,受到应有的表彰。直至1938年,埃利亚斯的父母还没有从其德国梦中警醒过来。那年他们去伦敦探望流亡的儿子诺贝特,后者劝他们留在伦敦。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双亲还是要返回德国,父亲的理由是: 他的所作所为光明正大,从没有什么不义之举;自认为是在一个法制国家中过了大半生,分享了它繁荣的成果,致使自己达到了小康。可是他错了,为此付出了惨重得无以复加的代价。 中学毕业后,早已决心走“homme de lettres”(文人,学者)之路的埃利亚斯于1915年6月进了布雷斯劳大学,所学专业为哲学和日耳曼学。可是一注册,他便像所有其他同学一样报名参军。他成了通信兵,被派往东线,在夏季战役中所在部队损失惨重。由于体格不强,他在战场上曾虚脱过一次,继而便被遣返回家。他不再适于野战,于是便当了布雷斯劳驻军的卫生兵。服役的同时,他开始学医,直至1919年4月才和军队彻底脱钩。 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血洒“光荣的战场”,对战争的残酷埃利亚斯曾有如下的描述:“污秽,泥浆,鲜血,垂死的马匹,垂死的战友,密集的炮火;我还能回忆起向前线一步步推进的场面: 隆隆的炮声日夜不停,我们看到开炮时的闪光。我身旁的战友吹起了口琴,大家唱道:u2018我曾有一个战友……u2019”体弱的他,身心无损地从战争中走出来,这近乎一个奇迹。不惟如此,经过“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炼,经过战火的洗礼,他反而更加坚强了。在战争环境下他培养出一种自律的能力,使自己的身心很快适应环境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无疑有助于他度过那漫长的流亡岁月,有助于他进行长期的、默默无闻的学术研究工作。 学医是父亲的意旨,后者中学毕业后曾想攻读医科,可他无钱读下去,于是便将当个济世活人的医生的理想寄托于儿子身上。埃利亚斯不愿放弃他心爱的哲学,学医的同时又兼学哲学,在其通过了医学基础科目考试之后,便逐步放弃医学而专注于哲学。可是临床前的医学基础和解剖学的学习,由此所获取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其以后的事业带来莫大的裨益。在其《生平漫笔》中他曾写道: 他对人在笑和微笑时的面部肌肉的运动了如指掌,并和类人猿进行了比较。人类笑肌的复杂多样使面部表情的丰富与动物面部表情的呆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引发他得出这样的认识: 人类的感情不仅仅是某些面部肌肉运动的原因,感情和表情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码事,自我的存在和他人是无法分开的。只是在文明的进程中感情和表情才人为地分了家。埃利亚斯甚至怀疑,如若没有医学知识,他能否构建起他的有关西方人心理发生的理论。 在布雷斯劳他师从新康德主义者理查德·霍尼希斯瓦尔德(Richard H·nigswald, 1875―1947)。为扩大眼界,1919年夏季学期他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听过他心仪已久的贡道尔夫(Friedrich Gungdolf, 1880―1931)的课,后者是歌德专家,同时也是诗人,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11年后,年轻的冯至来到海德堡,也对贡道尔夫的道德文章大加赞扬。埃利亚斯还参加了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讨论班,雅氏建议他就文明文学家为题作个主要发言。所谓“文明文学家”原是托马斯·曼用来讽刺包括其兄长亨利希·曼在内的左派作家的,在这里文明是作为文化的对立面出现的。在托马斯·曼看来,文化是自然的、真实的,因而也是德意志的;而文明则是异邦的,没有魂灵的,分裂的。 迄今为止,埃利亚斯很少过问政治,其父母亲眷的圈子也都远离政治。在战时的1918年他曾因其口才出众被战友选进了士兵委员会,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对政治敬而远之的态度。面对这一政治化的题目,他避开现实,而是从历史根源上来阐发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 1920年夏季学期他又就读于弗赖堡,目的是要参加在弗赖堡大学任教的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歌德讨论班。由于布雷斯劳大学的导师霍尼希斯瓦尔德的预先警告,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抱着批判的态度。介绍他来见胡塞尔的曾是胡氏的学生和助教艾蒂特·施坦因女士。她在推荐信中写道:“而今有个青年到弗赖堡去,为的是听您的课,我曾答应他将其介绍给您,本来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他叫诺贝特·埃利亚斯。主科或副科是医学,在霍尼希斯瓦尔德那里进行哲学训练,不过我劝导他: 暂时收起他的批判主义,以便对现象学有所了解。”艾蒂特是个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后被纳粹残害于集中营。保罗教皇在1987年访问德国时,曾对她加以表彰。 在其撰写哲学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埃利亚斯的解剖心理学的观点和导师的观点发生了冲突,实际上是和新康德主义发生了冲突。新康德主义流行于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后分为两派: 马堡学派和弗赖堡学派。他们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但又指责康德唯心得还不够彻底;他们否认康德“自在之物”唯物主义的意义,将其说成是一种“极限概念”,它所表明的乃是认识的极限,而并非实在之物,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埃利亚斯的导师霍尼希斯瓦尔德既不属于马堡学派,也不属于弗赖堡学派,甚至提出了“具体主观性”和“事实认识”的立论,但骨子里还是新康德主义。埃利亚斯在其博士论文《观念和个体》中表达了他从解剖心理学角度出发所得出的认识,这和哲学唯心主义有所背离;他强调大脑运作的方式,这也和新康德主义者所称的先验就有的作为观念领域的人的“精神世界”无法合拍。埃利亚斯认为: 先验的一切无法符合事实,“我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康德所说的超越时间和超越经验的一切,是一种有着因果关系的表象,这种有着时间性或自然和道德法则的表象和其相应的话语被他人习得才能保留于个人的意识之中。这些概念(或表象)是一种知识财富,因而也属于一个人的经验宝藏。”在这里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先验论。导师无法接受他这位博士生的观点,并指出“生物学并非万能”,要求他进行根本性的修改。那时师徒如同父子,不进行修改,论文就无法通过;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又有违自己的本意。面临这两难处境,他进行了“小修小补”,致使导师满意,而他的基本观点也得以保留。1922年他通过了如下学科的口试: 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化学,1924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埃利亚斯的博士论文充满着哲学术语和抽象的论证,但特别重视事物发生的先后次序;在该文中埃利亚斯就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先前的国家形式如何发展成后来的形式;先前的经济形式如何发展成后来的形式;先前的知识形态如何发展成后来的形态;先前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如何发展成今天的形式,这也透露出他日后研究的信息。 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不媚俗、不欺世,明知自己的观点不合时宜,也大胆地发表出来;面对对自己未来有决定性影响的权威也能坚持原则,但又会在枝节问题上进行某种妥协,表现出适度的灵活性,这是一种忠实于学术的可贵的品质。在此后的数十年之久,埃利亚斯不为世人所理解,在学术界一直处于边缘人的地位,可他无怨无悔,不改其孜孜以求的乐趣。 20世纪初,有个名为菲舍尔的德国人组织了一个候鸟协会,奖励青年徒步旅行,一时间满山遍野闪动着青年人的身影,传出阵阵歌声,这使人想起我们曾经有过的“拉练”。不过这种协会排斥犹太人参加,犹太人不甘寂寞,也组织起一个蓝白协会来与之唱对台戏,不仅进行“拉练”,也进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据同时代的人回忆,埃利亚斯参加了布雷斯劳蓝白协会,并且是其中的重要头头,不过他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是争论的话题。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 他于1921年7月在该协会的《蓝白杂志》上发表过题名为《在自然中观察》的文章。该文完全没有涉及这一刊物最为关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而是概述了他的学术观点,显现出他以后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轨迹,是其从哲学家向人学家转变的第一篇文献。这里所说的“人学”,并非“文学即人学”意义上的“人学”,而是直接研究人的科学,它包括以下诸学科: 历史、心理学、心理分析、人种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埃利亚斯就是试图将这些学科熔为一炉,来创立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他认为,人面对世界并非一个封闭的个体,而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属于这个世界。他不承认先验的东西,一切的理论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如果说他在以前的思考中还有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而则是开始朝着经验和实践的方向转变。经验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评价客观事物的科学的尺度。 《在自然中观察》一文不仅表明了埃利亚斯的科学态度,也显现出他的远大目光,开阔胸襟,承前启后、一往无前、将学术研究进行到底的志向。他在该文中引用一句拉丁成语,以为其一生的座右铭:“lapadia echontes diadosusin allelois”,用中文来说就是火把接力的意思,也可说是薪尽火传。前薪虽尽,后薪以续,前后相继,学术之火,永不熄灭。他对其博士导师霍尼希斯瓦尔德满怀感激之情,他也从导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1966年之后,在其获取阿多诺学术奖金之后的一次答谢演讲中他曾这样说:“人学以及其他的学术工作都是一种火炬接力: 从上一代接过火炬,前进一程,又将其传到下一代的手中,代代相传,学术的火炬永远照耀着人们前进。前一代为后一代创造了超过自己的前提。”
职业生涯1922年进行了博士考试之后,他再也不能指望得到父母经济上的支持,因为大萧条也使他们自身难保: 难以想象的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使得父亲的退休金萎缩得微不足道。于是他不得不设法自己养活自己。一家生产炉盖和阀门盖的工厂需要一位高学历的年轻人,最好是博士。经人推荐,埃利亚斯前往应聘,结果他便成了这家拥有800多员工的中型企业的销售部主任。于是他经常出差到北欧诸国,开展其营销活动。为此他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他也观察到了经济危机中的工人那令人触目惊心的穷困。他也了解到工厂主之所以孜孜为利,也并非只是为了赚钱,为了竞争所带来的乐趣,而是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然。埃利亚斯迄今为止主要是栖身于学校的围墙、学术的象牙之塔之内,士兵的经历打开了通向社会的一条门径,而这次的“学商”则使大门洞开,对其以后的学术生涯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文明的进程》的许多观点就是源于这次的营销经历。 销售部主任是个令人眼馋的职位: 薪给优厚,又能经常到国外出差,他本可以衣食无忧、开开心心地干一辈子,可这样的生活非其所愿。他锁定要在大学里发展,教学科研才是其所爱。他自信能做一个好老师,为人授业解惑,在同学中他享有这样的声誉: 复杂的事物能以简单的话语表达。1924年他离开了工厂,来到了阔别五年的海德堡。这期间,父母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也可供他们惟一爱子的不时之需。在这里还需提一件事: 埃利亚斯是个珍惜时间的人,在工作之余,在旅途中,他将一些希腊的故事和笑话加以翻译改写,后来竟在柏林画报上发表,并得到稿酬。这使得他坚信,笔耕也能使他维持生活。 童年和青年时代过去了,在海德堡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主要著作
《文明的进程》(上下册)、《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圈内人与圈外人》、《德国人研究》、《什么是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论文集》(上下册)等,此外还留有众多手稿。2005年,19册的全集由Suhrkamp出版社出版。还著有《莫扎特的成败: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