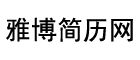陆圻的个人简介
陆圻(1614―?)字丽京,一字景宣,号讲山,浙江钱塘人。明末清诗人、名医。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卒年不详。少明敏善思,早负诗名。与陈子龙等为登楼社,世号“西泠十子体”。性至孝,尝割股疗母病,久而知医。后尝入闽为浮屠,母促之归。当卖药长安市上。适湖州庄廷x私撰明史,因圻名盛,列之卷首,与查继佐、范骧皆被株连。事白后,遁之黄山学道,他的儿子陆寅号泣请归。不久,又往依岭南金堡于丹崖精舍,忽易道士服遁去。(或云:隐武当山为道士)遂不知所终。陆圻与弟陆培、陆杲杂形拿焙拧奥绞先拧薄V小洞油贰锻锾眉贰段髁晷掠铩贰妒瘛范嗉啊读槔继媚亍返龋肚迨妨写凡⒋谑馈个人简介
陆圻(1614―?)字丽京,一字景宣,号讲山,浙江钱塘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卒年不详。少明敏善思,早负诗名。与陈子龙等为登楼社,世号“西泠十子体”。性至孝,尝割股疗母病,久而知医。后尝入闽为浮屠,母促之归。当卖药长安市上。适湖州庄廷x私撰明史,因圻名盛,列之卷首,与查继佐、范骧皆被株连。事白后,遁之黄山学道,他的儿子陆寅号泣请归。不久,又往依岭南金堡于丹崖精舍,忽易道士服遁去。(或云:隐武当山为道士)遂不知所终。陆圻与弟陆培、陆杲杂形拿焙拧奥绞先拧薄V小洞油贰锻锾眉贰段髁晷掠铩贰妒瘛范嗉啊读槔继媚亍返龋肚迨妨写凡⒋谑馈
生平
陆圻,字丽京,一字景宣,本号讲山,清代仁和(杭州)人。顺治时拔贡。父亲运昌,是明代万历进士。陆圻自少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六七岁就能写诗,父亲很喜爱他。陆圻素负盛名,士人争相接近他,与弟辍⑴喽家晕恼戮雷匀危D诔莆健C鞔珈跫洌恼伦诮常甲鸪缏(江苏太仓)张溥。张溥卒后,陆圻前往吊唁,赋五言长律,一时传抄,以为杰作。又与陈子龙等结登楼社,世人号为西泠体,为西泠十子之冠。陆圻对父母极为孝顺,曾割股治疗母病,久而知医。明亡后,绝意功名,行医卖药于江浙间,颇著奇效,吴中(苏州)人称他为讲山先生。湖州(属浙江)庄钟私自编写《明书》,为人告发,陆圻与查继佐、范骧都被株连,很久才获释。父母去世后,就弃家远游,入粤拜谒天然和尚,扳依佛门,法名今龙(一作今竟、又作德龙),字与安。又访部澹归于丹崖精舍。澹归,法名今释,原为明朝进士、知临清州事金堡,遁迹佛门。南雄太守陆世楷造丹崖舍给他居住。陆圻前往皈依澹归。
陆圻弃家出游后,文士们都追慕他。当时洪P思(升)有答友人绝句说:“君问西泠陆讲山,飘然瓶钵竟忘还;乘云或化孤飞鹤,来往天台、雁宕间。”(见《静志居诗话》)
著作
陆圻所著医书,可医者有《本草丹台录》二卷、《医林口谱》二卷(《浙江通志?子类部事类》有《口谱》二十四卷、《两浙轩录》)作《陆生口谱》),《医案》一卷(俱见《海宁续目》),《医林新编》若干卷(见《张氏医通》引用书目,《海宁续目》作《医道十篇》,《浙江医籍汇考》作二卷),《伤寒捷书》二卷(《杭州府志》)。其他著作尚有《从同集》、《威风堂集》、《本陵新语》、《洛神赋辨注》、《诗礼二编》、《新妇谱》(俱见《浙江通志》),《诗经吾学》三十卷(见《仁和县志》),《内诗》五卷(见《经义考》),《冥报录》一卷(见《说铃》)。
故事的另一面 :阿袁和陆圻
嘭嘭嘭!嘭嘭嘭嘭嘭!带着些许不详的征兆,敲门声像急雨般砸下来。张国兰拉开防盗门,女儿陆圻站在外面,全身竟是湿透的,头发到衣角正往地面噼里啪啦砸着小水粒。“天,这是怎么搞的?”张国兰一把将女儿拉进来,死鱼般冰冷滑腻的手感。
“倒霉啊,刚经过一间洗车店被水枪冲了。”大概因为冷,陆圻说话的声音有点发抖,她皱眉脱掉浸满水的运动鞋和袜子,在鞋柜里找了凉拖穿着往浴室里走去。
张国兰和坐在沙发上看球赛的陆君伟对望一眼,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却是说不上来。
女儿今年23岁,大学毕业后在新林市电视台做了三个月的实习编导,眼看要转正却以“不想说谎话”为由辞了职。父亲陆君伟就工作的事和女儿多次交换意见,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通过关系进几间还算不错的国营企业,但陆圻并不热心,始终懒散,每天睡到九点起。有一次父母的意见提得厉害了,她将自己关进房里两天两夜,张国兰教书多年,本有轻微的神经衰弱,那次真是被吓坏,再也不肯逼迫女儿一丝一毫,而一向好脾气的陆君伟也只能这样想――反正家里不是养不起。随后陆圻在网上找了兼职的广告文案来写,收入并不比坐班差很多。
淋浴声哗啦啦地持续着,外面的电视声越来越微弱,夫妻俩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耳朵却飞过去紧紧贴在浴室门上。今天陆圻在里面呆了起码比往日多一倍的时间,张国兰看看电视又看看墙上的钟,手掌不住地在腿上来回摩挲,丈夫拍拍她的手背,示意不要太忧心。
哐啷一声,张国兰从沙发上弹起来,四处张望,原是大风扑进阳台吹翻了一小盆花。心跳怦怦地超过了120,今晚的确是有些神经质,她掩饰着心慌边走边说:“刮这么大的风,看来雨是下不来了。”出去将那盆蝴蝶兰扶起,防腐木地板上散落了些泥土,被风吹着像珠子似的滚来滚去。拿扫把扫几下,地板干净了,心也镇定下来,张国兰站在扶栏边望着外面清朗高远的天空,大朵白云被疾风推着像涨潮之前的海浪往岸边层层翻滚,她忍不住唤丈夫:“老陆,你也出来吹吹风,好凉爽的夜啊。”
正说着,但见陆圻趿拉着拖鞋走进客厅,她拉开冰箱拿牛奶出来喝,破天荒地往父亲身边一靠,问到:“几比几了?”“呃?”陆君伟心思早没留在比赛上,哪里知道几比几,只好嗯嗯啊啊地跟女儿打马虎眼,不能干脆地说不知道,毕竟女儿很少主动与他亲近地坐下来。
陆圻不计较父亲敷衍的回答,她显然对足球比赛兴趣不大,两分钟内拿着遥控器调换了无数个频道,音乐台正在放某个明星的演唱会,张国兰关了落地门快步走入,口中招呼着:“哎,就看这个,听会儿歌挺好的。”她甚至不记得那个明星的全名,只有模糊的印象――女儿喜欢。电视画面定格在那个吐词不清奇装异服的歌手脸上,三个人像雕塑般认真欣赏到了姿势僵硬的程度,风不停在外面咆哮着,仿佛要破门而入似的将落地门吹得轰轰作响,他们努力不被打扰地盯着电视。如此滑稽地坚持了一会儿,陆圻伸着懒腰站起身说:“爸妈,我先去睡了。”
“嗯。”
“嗯。”
父母同时答话。
陆圻房间的灯一夜没关。
第二天张国兰在学校办公室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标题是:男子离奇溺水身亡,家属高额悬赏知情者。如今的世道,这种小灾小难小意外的发生实在不足为奇,新闻本身也是很窄的一幅夹在众多民生关注中间,搭配的黑白照片极是模糊,张国兰推近眼镜去看,猛地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林水河。清晨7点时男子的尸体在林水河东二段被人发现,离她家所在的西三段不过相距2KM,搞不好就是从西三段淌下去的呢。死亡好像突然逼近身后吹了口冷气,张国兰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又连着哆嗦好几下,触电般想起昨夜抓住女儿手臂是滑腻冰冷的感觉。
办公室里没有人,张国兰抓起电话拨回家,她决定问问陆圻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电话响了一声、两声、三声,没有人接。是还在睡觉吗?不该啊,课间操的铃声已经响过,这都上午第三节课了,要搁平常她早就起来,张国兰越想越不对,慌忙地在桌上留了张字条给同事罗老师,准备回家看看。
刚走到门口,电话铃忽然响了,尖锐单调的声音像把钳子将她抓回来,接起竟是陆君伟,他在那边一改往日温吞的语调急冲冲地说,“国兰,不对啊,我仔细想过了,咱们家楼下根本没有洗车店。”也就是说,不管陆圻是在哪里的洗车店被水枪冲到,她回到家都绝不可能浑身上下还不停滴水,张国兰只觉得两腿一软,颓然坐倒在椅子上,她慢慢揉烂了刚才写的留言条,一股湿冷的感觉平地而起,淹没了她的膝盖,玻璃窗有轻微的动静,是这年秋天第一片落叶刮在新林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教师办公室的窗台上,张国兰坐在那里怔怔地看着叶子在细细的瓷砖上努力攀附着,最终轻轻地往楼下跌去。
下午回家时,张国兰特地走到林水河边看了看,前几天接连下大雨,水面漂着些落叶,但居然很干净,空气里有隐隐呛烟的味道,像过去在农村里烧秸秆的黄昏。河面异常平静,与其说这里刚刚发生过什么,感觉更像是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着什么,不远处有几个人站在河边指指点点地说话,直觉告诉张国兰他们在讨论报纸上的那桩新闻,她想走过去听听,却出于一种莫名的恐惧,反而远远地走开。
回到家,陆圻已经把晚餐做好了,米饭的香味从厨房里弥漫出来,桌上简单干净的一汤两菜。坐在桌前的陆君伟向张国兰使了个按兵不动的眼色,她默默坐下来,三个人埋头扒饭,气氛里有种说不出的压抑。吃着吃着,张国兰终是忍不住问女儿上午去了哪里。
去买菜啊,陆圻回答,自自然然的神态。
这让张国兰稍稍放心一点,她随即提起报纸上的悬赏事件,陆圻的神色也并没有异样,她想,大概真是自己太敏感。
两天之后的夜里,警察敲门。
“这是陆圻的家吗?”较高个子的男警问,帽檐下盖着瘦得两颊往里凹陷的脸,看不见眼睛,薄薄的嘴唇显得非常冷淡。较矮的女警倒是笑眯眯的,两腮圆圆地鼓着,形状接近临产之前的金鱼肚子,仿佛随时会爆炸裂开。
“是。请问你们……”张国兰的心跳又加速跳动,她擦着汗,这更年期真是说来就来。
“是这样,”女警官开口了,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这里有个案子想找她了解一下情况,据群众反应您女儿也许知道一些情况。”
“什么案子?”陆君伟的手从后面搭上来,张国兰禁不住微微一颤。
“我们还是直接和陆圻谈吧。”男警官接过话,语气里有不容置疑的威严。
陆君伟让妻子进去房间里叫女儿,他则谨慎地要求再看看两位警官的证件,这年头行骗的太多,上个月他们研究所的郭主任家就险些被两个冒充的电信工作人员抢劫,幸好紧要关头郭主任想起自家一直是用网通,哪来的电信网络维修服务啊,遂将门死死地关上,全身立即爬满了余悸的虚汗。
男警察叫梁东,女警察叫罗雯。两人笑着夸奖陆君伟防范意识挺强,倒半点不像是来调查案件的样子,老陆暗暗松一口气。这边刚进门,陆圻穿好外套从卧室里出来了,她和两个警官对望一眼,神态是十分了然。
这边吧,陆圻招呼着,几个人在餐桌旁边围桌坐下。
2、
“这个人你认识吗?”梁东拿出一张男子的照片,看上去大约有25、6岁,穿件白背心站在棕榈树下,及膝花短裤,人字拖。
“不认识。”陆圻答。父母在身后站着,紧张得指甲抠到木头椅背。
“那么,9月29日晚上10点你在哪儿?”梁东将照片搁在桌面,用手指轻轻扣着。
“我出去喝了点东西,在u2018拉提u2019咖啡。”
“你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
“怎么一个人去喝咖啡,应该有朋友才对呀。”罗雯笑眯眯地插话,但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试探怀疑。
“我都是一个人去,不信你问我妈。”陆圻说,语气里有不愉快的冷淡。
张国兰赶紧点点头,“她喜欢跟自己呆着,这点大家都知道。”
“可是,”梁东沉吟了一下,“u2018拉提u2019的老板赵小姐说你那天不是单独离开。”
“呃。”陆圻挠了挠头,好像难以启齿,“当时是有个男人跟着我,挺烦的。”
“他跟着你干嘛?”罗雯马上追问,声音提高了两个度。
“我又不是犯人,逼三赶四地作什么!”陆圻恼了,跟着变得大声。
“陆小姐,我们之所以来调查情况,是对案件已有基本的了解。希望你配合。”梁东再次插话,淡静的语气使她沉默。
“他骚扰我,说想跟我交朋友。”
“噢?你怎么说?”
“我当然说不啊,我不认识他,也不想认识。”
“那他跟了你多远?”
从拉提咖啡到银河花园是一段接近500米的大坡道,尽头左转再往前走几百米就到了小区大门,右边是林水河。陆圻想了想说,“我说不想认识他,说得挺坚决的,就以为他没跟着了。后来我去便利店买了点东西,再走到路口转角,那个人居然等在那里,我当时很害怕。”
“接着你们发生冲突了?”
陆圻瞪着桌面,“他好像喝多了点,一再伸手来拉我,我躲着躲着就靠近河边,你知道林水河那边有段围墙一直没被修起来,当时我们正好在那附近拉扯,我急着想要摆脱他,一不留神就顺着草坡滚到河里去了。”陆圻抱歉地望了父母一眼,传达着“没说实话是因为怕你们担心”这样的情绪,她接着说:“然后他跳下来把我拉上岸……我就回家了。”
“那个男人也上岸了吗?”梁东问。
“不知道,我先爬上来,在那里等了一下,担心他上岸继续纠缠,就赶快跑了。”
梁东再次将那张照片推到陆圻面前,“你再看看,跟着你的男人是不是照片上这个?”
陆圻接过去仔仔细细地看了十几秒钟,颇有些无奈地说到,“真的认不出来啊,咖啡店里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个人,他跟着我出来时天很黑,况且我也不敢去看他什么模样,只记得他穿了件大红色的T恤蹲在路边抽烟,浑身酒气。”
梁东和罗雯交换一个眼神,两人站起身来,“好的,我们知道了,谢谢你提供线索。”
“这个,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陆圻怯生生地,“照片上这个男人怎么了。”
罗雯微微扁嘴,“溺死了。”
送走两个警察,家中的气氛没有因此松弛。张国兰拉着女儿的手到沙发坐下,斟酌着说:“小圻,我和你爸相信你的话。不管怎么样,事情已经发生了,妈希望你不要有太重的思想负担,那个人没安好心,就算出了意外,也不是你的错……”陆君伟轻哼了一声打断妻子,他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太妥当,但也找不出更好的宽慰,只一味用手在女儿的头上轻轻抚摸。
“你们放心,我没事。”陆圻点头,随即回房。
一夜无眠。陆圻躺在床中央,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灯后的墙壁有一圈黑黢黢的影子,组合起来像只不怀好意的眼睛死死地监视着下面的人。她将被子拉得很高,慢慢掩住自己的视线。再热的天气里也一定是要这样厚实沉重的被子,陆圻必须、只有藏在这石碑一般的遮挡下面,才觉得自己可以勉强逃开那束黑暗中狼一样的眼神。
十年了。距离事情发生已经有十年。陆圻并不想刻意去反刍记忆,但的确很多时候会想起来,在她刚刚读初中的那个秋天,晚自习过后的回家路,猛然从旁窜出的黑影。肮脏腥臊的大手捂着她的嘴,街边花园的丛林里有狗尿的气味,她挣扎,试图叫喊,最终在那双邪恶眼睛的逼视下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暗无天日的一刻。
当时陆圻的舅舅还在新林市刑侦大队上班,他说不报警比较好,报警了,反而许多程序和结果都由不得自己决定。他们疯了一般在街上搜寻,浑身仿佛喷着无形的火和刺刀,陆圻记得自己走在几个亲人中间,纤细的拳头紧捏着几乎要滴出血来。那个人却消失了,也许是闻风而逃,总之没有出现在新林市可能的任何角落。张国兰问女儿:“小圻,你没认错吧?你真的认得?”陆圻冷笑,怎么可能认错,街心花园里那个她每天都会给他买个馒头的乞丐,当初打动她的也是那双饥饿可怜的眼神。
那时起陆圻开始变得冷漠,好几年的时间,她不能和别人交往,渐渐养成孤僻乖张的习惯,没有朋友,更没有办法相信谁。考大学时本来可以报到外地,但她执意填了本市一所师范院校,因为可以走读,平常仍旧住在家里。辞职后的定期外出是她下意识地做的反自闭训练,通常都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个人喝点东西,逛逛书店,她不喜欢交朋友,稍有人靠近,就会本能地走开。
“老陆,你相信吗?”另一间屋里,张国兰心事重重地问。
“我相信。”陆君伟闷头抽烟,接着说:“况且,就算她做错什么,我也会原谅她。”
“……”在学校教了一辈子政治课的张国兰说不出同样的话,她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可是联想到弟弟张国强在出事之前和她的那次谈话,张国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所谓的游戏规则,你遵守规则,就能不停通关,想要试图突破规则,最后就只能出局。
当然,弟弟的这段话是针对他在一桩刑事案件上遇到的难题,犯罪嫌疑人是个颇有背景的商人,与政府各部门渊源很深,张国强破案的过程中,对方暗示他只要睁只眼闭只眼,以后不愁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张国强肯定也是犹豫了,所以才有和姐姐的那番话,不过后来到底是什么支持他没有选择遵守规则而是勇于去打破,没有人知道。就在案件告破的第二天,张国强在自家窗台上擦玻璃,窗框忽然脱落导致他从13楼摔下去,除了意外,没有任何合理解释。
多少年来这件事一直是张国兰心里的顽疾,她不相信,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世上确有难以预计的事件天天发生,命运这个顽童,由不得你猜度,由不得你反抗,甚至由不得你俯首陈臣,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让人生活在意料之外,就像在汪洋上撑着独木舟航行,每时每刻都可能被巨浪掀翻。
陆圻刚刚出事那年,张国兰为了让女儿开心,特意在家里养了一窝很乖的小狗。有一天张国兰给小狗喂食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只,找了半天竟在陆圻的拖鞋里,全然不知何时被她踩死了,软软的一团肉泥,拿在手里还很温热。不久后那窝小狗相继死去,各种各样的死法,掉进煮沸的开水,被电风扇叶子绞烂,卡在防盗门的铁柱中间……无一例外,但都是意外事件。
张国兰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情和女儿有关,或者说她宁可以为是家里长久不散的压抑气氛使得不幸事件一再发生,她觉得不安,但更多是心疼和无力。家中自是再也没有养过任何活物,随着岁月流失,日子也慢慢平静下来,直到陆圻念大学的第二年。那个周末陆圻兴致很好,提议由父亲开车带她们母女去郊县看望独居的外婆,临走时她不忘去市场里给外婆买些海产品和热带水果,那时市场上对老鼠药还没有明令禁止,陆圻说外婆家是平房,这个也可以备一些。说话的时候陆圻笑容乖觉,他们陡然感慨,仿佛有拨云见日的欣慰,外婆家一行玩得温馨痛快。
从外婆家回来没几天,陆君伟听同事说城里一家餐馆后巷里死了个流浪汉,不知是捡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吃,死前吐得满地都是污秽,那些东西曲曲折折地顺着羊肠小道流到外面,臭了半条街。当天的地方新闻立即播出这条消息,报道上说该流浪汉是误食了老鼠药所致,随即市政府颁布不准售卖老鼠药的禁令,彼时张国兰和陆君伟不约而同从两个方向看了女儿一眼,她端正地对着电视,向来素白隐忍的脸上,好像正在缓缓地浮出另一个人的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