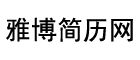路易·马勒的个人简介
路易·马勒,法国导演,新浪潮重要影人之一。作品具有浓厚的个人特征,主题常常涉及社会边缘化问题,对性的描写曾引起指责,但评论界认为背后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高等电影学院。1957年开始独立导演故事片,处女作《死刑台与电梯》获路易·德吕克奖,跻身新浪潮导演的行列。接着的《恋人们》载誉威尼斯电影节。路易·马勒 - 简介
路易·马勒. 生于1932年 10月30日 ,法国
逝世于1995年11月24日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USA. (lymphoma))
法国导演,新浪潮重要影人之一,擅长开拓新路子。
作品具有浓厚的个人特征,主题常常涉及社会边缘化问题,对性的描写曾引起指责,但评论界认为背后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高等电影学院。1957年开始独立导演故事片,处女作《死刑台与电梯》获路易·德吕克奖,跻身新浪潮导演的行列。接着的《恋人们》载誉威尼斯电影节 。1973年的《迷惘少年》把他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
路易·马勒 - 生平
上世纪60年代,路易·马勒被称为影坛新浪潮的开山人物。在此后的30多年里,他高产优质地拍摄了多种风格和主题的影片,成为法国电影的中坚力量。离开法国后,马勒来到美国,他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也是少数在美国还能保持自我风格的“国际导演”。
法国人送人礼物很大方,喜欢送些传之后世的礼物给人作纪念。美利坚建国之初,法国人送给这个年轻国家一份兴师动众、费时耗财的大礼―――纽约港口屹立的自由女神像,与法国国旗的蓝、白、红三色分别指涉的自由、平等、博爱,形成强有力的呼应。还有一件礼物是由一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贵族独自悉心架构、精心打造的鸿篇巨制,名为《论美国的民主》,是一部传世经典。法国人有时待人接物又很“地方”,不乏对地域的细密划分,特别是巴黎人,他们有时将国人分为巴黎人和外省人两种人,然后又在巴黎人中细分在第几条大道上住的,或以塞纳河为界分左岸和右岸。有不少文人或想成长为文人的住在左岸,立足于左岸多少表明自己的情感诉求、文学主张乃至文化理想。“左岸派”的命名更多地得益于法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连带了影像流派的兴起。电影左岸派大多从文学的此岸摆渡到电影的彼岸的,或者在两岸之间来回走动。这拨人中有人在新浪潮电影还未汹涌澎湃之前就弄潮掀起微澜,后又在左岸上观看惊涛拍岸,他就是路易·马勒。
1932年10月,路易·马勒出生于法国北部的蒂姆里,盛产糖类,属于“甜蜜”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满足相当多法国人的味觉系统的重要需求。马氏家族从事这项甜蜜的事业,路易是含着金勺子来到人世的,自小就过得衣食无忧,甜甜蜜蜜的好日子,说他是位公子哥也毫不为过。但马公子没有继续经营家族的这份产业,而是与时俱进,搞起相当时髦的电影,参与丰富诸多同胞的视觉系统的影像需求,当然,玩时尚的东西向来都是以钞票为铺垫的。马勒从影之初拍片的所有资金源自家财,可以说,他全然在前人栽的树底下乘凉,导起片子来少了些局促,多了些从容,不像那些全无祖荫笼罩的寒门才子,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强不息,以享受日光浴来聊以自慰,算是与国际流行时尚接了一趟轨。
马勒当初从影出道早、起点高。1956年,24岁的马勒与雅克·考斯托联袂导演的纪录片《沉默的世界》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马勒的影像风格永远呈飘忽不安的状态,让影评人难以把握,无电影节法归类。他的影像风格与其婚姻状态极为相似,印证了法国文论大家德·布封的那句“风格即其人”的名言,同样让人琢磨不透。以往,人们常会用梅开二度来形容再婚的伴侣,马导则走得更远,换了三任不同国籍的太太,可谓梅花三弄了。这还不算与名伶让·莫娜的恋情。
让·莫娜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标志性人物,她曾经与马勒合作过《通往死刑台的电梯》(1957)和《恋人》(1958)等影片,也曾经是马导的情感伙伴。《通往死刑台的电梯》公映了几个月后,安东尼奥尼在巴黎碰见马勒时,对莫娜在《通片》里摇晃臀部的走路方式赞不绝口,后来还在《情事》(1960)一片里让女主角也按此种步态来表演。这位以创造尤物角色著称的名伶,后来又在弗朗索瓦·特吕弗的代表作《朱尔和吉姆》中饰演女主角,还曾放出一句话:“在我的生命中,除了特吕弗,再也没有谁更令我感兴趣了。”想必特吕弗的特殊魅力更令她难以忘怀,真不知马导作何感想。
《通往死刑台的电梯》一片开场就是莫娜脸部特写,正焦躁不安地与情夫来了一长段的恋人絮语,她在挂起话筒后又将头靠在墙上电话旁好似偎依在情夫的肩上;她沿街寻找失散的情夫,路遇他同样品牌的轿车而轻轻地加以抚摸……这些颇具画面感的镜头传达给观众的是,那个情夫何以甘愿铤而走险去谋杀情敌―――莫娜的大亨老公。该片颇受影评人和影迷的好评,获得“路易·德吕克奖”,还被誉为“法国新浪潮的导火索”。
马勒的影像师法前辈的地方很多,有三位经典大师级的人物不能不提,其中《通往死刑台的电梯》的影像风格和悬疑元素继续沿着布莱松和希区柯克的道路走下去,该片有好几场电梯里的戏都是刻意摹仿布莱松《死囚越狱》(1956)的狱中场景;《恋人》则显示出让·雷诺阿的深刻影响,马勒曾细看雷诺阿的《游戏规则》不下15遍,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马导借《恋人》一片在向雷导行大礼:两片的故事都是三角恋情,原先的夫妻感情转淡,红杏出墙的女主角最终坠入不太光彩且暧昧不清的情网。另外,马导还有两处师法雷导的《游戏规则》,一处是将场景由巴黎移至郊外;另一处是丈夫出人意表的邀请自己的情敌或是婚敌到乡下别墅做客。
大师雷导曾不无通透地说,所谓影像风格的形成往往是在一个人师法前贤技巧之后再抛开这些技巧。应该说,马导基本做到了这一点。雷诺阿的影像在苍凉的现实中触摸灵动的诗意,又在诗意的想象里了悟世事的沧桑,而马勒的影像则不断地向约定俗成的社会戒规乃至文化禁忌发起挑战,彰显了他那一以贯之的叛逆精神和无畏勇气。
其中,突破传统电影语言、批判成人陈腐世界的《地下铁的莎姬》(1960)、极具灰暗和颓废色彩的《鬼火》(1963)、表现母子乱伦的《心之低语》(1971)、反思“普通人的邪恶”的《拉孔布·吕西安》(1973)、颇具纪录―――剧情片风格的《与安德烈共进晚餐》(1981)以及再度触及公媳乱伦题材的《烈火重伤》(1992)等影片,处处留下了马勒挑战世俗、挑战自我的足迹。
1970年代中期,以罗兰·巴特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为代表欧洲文论大家,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探询、推论中国文化、妇女和语言的现状及其走向。1960年代末,路易·马勒将摄影机扛到印度去,力图在影像领域切实地把握东方古国的社会变迁,他秉承“直接电影”的理念所拍摄的系列纪录片《印度印象》,力求客观、真实地再现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引起极大关注,甚至招致印度政府的强烈抗议。
路易·马勒在他那影像探索的道路上,向来不甘于成为形式的奴隶、风格的走卒乃至语言的囚徒。创新求变、离经叛道,将摄影机对准人类灵魂的每个角落,是他矢志不渝的艺术主张和文化诉求,因而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道德勇气和力量。
每当人们问马勒创作的那些题材多样、风格迥异的影片究竟有何共同之处时,他总是回答说“我。”马勒坦承自己有重复自己的倾向,因此,努力自觉地抗拒回到业已探索的领域。
马勒曾经说过:“我真的觉得一个艺术家的天职是去创造一个世界,一个以风格及眼光来定义的世界。同时,我很崇拜那些不断求新的艺术家,他们不会一直守着同样的技巧,同样的表现手法。”
诚哉斯言,马勒的影像探索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走过来的。
《江南时报》(2005年07月20日第二十三版)
路易·马勒 - 作品年表
1994 Vanya on 42nd Street 万尼亚在42街口
1992 Fatale 又名:Damage(USA) 毁灭(烈火情人)
1989 Milou en mai 又名:May Fools 五月傻瓜(米罗在五月)
1987 Au revoir les enfants 又名:Goodbye Children 再见,孩子们
1985 Alamo Bay 阿拉莫湾
1984 Crackers 穷酸白人
1981 My Dinner with André 与安德烈晚餐
1980 Atlantic City 大西洋城
1978 Pretty Baby 漂亮宝贝(雏妓)
1975 Black Moon 黑月亮
1974 Lacombe Lucien 拉孔布·吕西安
1971 Souffle au coeur, Le (Murmur of the Heart)好奇心
1968 Spirits of the Dead 勾魂摄魄之“威廉·威尔逊”
1967 Voleur, Le (The Thief of Paris)大窃贼
1965 Viva María! 万岁!玛利亚(江湖女间谍)
1963 Feu follet鬼火
1961 Vie privée (A Very Private Affair)私生活
1960 Zazie dans le métro (Zazie in the Subway) 扎奇在地铁
1959 Amants, Les (The Lovers) 情人们(孽恋)
1958 Ascenseur pour l’échafaud 死刑台与电梯
纪录片和电视剧:
1987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快乐的追逐(纪录片)
1986 God’s Country 上帝的国度(电视剧集)
1976 Close Up 特写(纪录片)
1974 Humain, trop humain (Human, Too Human)人性,太人性(纪录片)
1974 Place de la république协和广场(纪录片)
1969 Phantom India 印度印象(电视剧集)
1968 Calcutta加尔各达(纪录片)
1964 Bons baisers de Bangkok (电视剧集)
1962 Vive le tour (Twist Encore)(纪录片)
1956 Monde du silence, Le (Silent World) 沉默的世界(纪录片)
路易·马勒 - 访谈录
《好奇心》及《童年再见》里有自传性色彩的少年角色,主要是对文学及爵士乐--而不是电影--感兴趣。这是你自己成长的写照吗?
不!事实上我有三种热爱。音乐是其中之一。在十四、五、六岁这段期间,我的兴趣很快地从贝多芬转向路易·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及查理·派克(Charlie Parker),当然还有文学。和《好奇心》里的角色一样,我的生活被心杂音症打断了几乎两年之久。我被迫从寄宿学校休学,在家自修。由于不能做剧烈运动等一类的事,我在这段期间内读了很多书。《童年再见》及《好奇心》里的角色的确是来自我早年沉浸在文学里的这段时期。那时我几乎什么书都读--甚至在十四岁那年就读尼采(Nietzsche),真是荒谬!我对电影的热爱要稍微再晚一点才开始,记得那几年在巴黎的几个电影俱乐部(cineclubs)里发现了诸如《游戏规则》(La Regle dujeu)一类的电影,包括我一直认为是触发了我想拍电影的决心的那一部电影--罗杰·林哈特(ogerLeenhardt)导演的《最后的假期》 (Les Dernieres vacances)。我想那部电影是战争刚刚结束、我大约是十五或十六岁时拍的。这可以说是形成后来「法国新浪潮」风格的第一部法国影片。我对林哈特的敏感(sensibility)及这部描述一个有产阶级家庭在夏日假期中发生的事,感到非常亲切。虽然这部片子我只看过几次,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实际的指针,但是我认为《最后的假期》引发了我想拍电影的强烈欲望--那几乎是一种冲动。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重新发行。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不仅是对我而言,对所有新浪潮诸君也是如此。
是高达介绍罗杰·林哈特加入《一个已婚妇人》 (Une Femme mariee)的,不是吗?
是的。林哈特非常受到仰慕,虽然他只再导演了一部剧情片。但他拍了许多精采的短片、令人赞叹的短片,他也以此出名。
你父母及亲人对电影持何种态度?他们把电影看得和其它艺术一样严肃吗?
不,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不记得和父母讨论过电影。和兄弟们是有的。我哥哥柏纳德(Bernard)--大我三岁的那个--一直对我很有影响力,过去他总是告诉我要读什么、不要读什么,要看什么、不要看什么。我们常常谈论未来。他想成为作家,我也是。但是有一次他告诉我:「你非常好动,你不应该当作家,你应该拍电影。」这显然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父母相当有文化教养,但他们不是影迷。对我母亲而言,所谓的好电影就是像《文生先生》(Monsieur Vincent)一样的。她是一位非常、非常虔诚的女性。她不阻止我们看电影,但是当我告诉她说我要成为电影人(movie-makers)时,她真的非常震惊。她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上流社会,总认为我会是小孩当中从事家族生意的一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上我,也许是因为我的兄弟都是无可救药的学生吧!他们被各种不同的学校踢出来。我母亲已经决定让我去念Polytechnique一类的工业名校,然后进入家族事业。当我告诉母亲我想当电影导演时,我还没满十四岁。她那时可以说是惊骇万分!
你以前在塔美芮斯时可以到电影院去吗?或者说,你小时候跟当地社区是隔离的?
不!我们那时候有一家所谓的「赞助性的电影院」(patronage cinema),放映的影片都是由教会筛选的。但是我不确定塔美芮斯当时有没有商业性的电影院。因为离里尔很近,如果我们要看电影,应该是到里尔去看。但是一九四年以后,我就没有真的在塔美芮斯住过;我还不到八岁的时候,我们就搬到巴黎,往后求学的日子我都在巴黎及枫丹白露,只有在假期的时候回塔美芮斯的老家。
在占领时期中成长,你是否觉得被剥夺看风行的好莱坞电影的机会,而尽看一些相当特定的、拘限于某一类型的法国电影?
当然我记得看过法国电影,在当时很兴盛。事实上,那是法国电影的重要时期之一。当时也有德国电影,包括德国的宣传影片。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看过《吹牛男爵》(Baron Munchhausen),那时是一九四三或一九四四,在Champs Elysees看的。我不能说我们有特别感受到缺乏美国电影,因为我当时还没有真正接触过美国电影。大战以前,我还只是个小孩。我记得在里尔看过《白雪公主》(Snow White),那应该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接着战争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和美国电影隔绝了。但是我记得战争结束后,美国影片在绝迹五年之后突然间又出现了。《大国民》(Citizen Kane)刚上演时我没看到--那时候我可能在寄宿学校;但是当我在一个电影社看到时,它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作了。在维琪政府时期,我们看了许多纪录片,父母也鼓励我们看,因为这具有教育性。在Champs Elysees有一家专门放映纪录片的电影院,我记得很清楚,就在诺曼迪(Normandie)旁边。一位和我同年的朋友跟我说:「那些影片一定影响到你对纪录片的兴趣。」我回答说:「也许是在潜意识里吧!因为我真的不记得这些影片--除了记得他们有时候实在很无聊!」
当你一九四○年到巴黎的时候,有一种终于离开了塔美芮斯的轻松感吗?你的作品里--从《孽恋》到《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 USA)及《阿拉莫湾》(Alamo Bay)--有逃离小城生活限制这一类型的人。
嗯--当年我们还是小孩子,父母认为我们住在巴黎比较好,于是我们搬进祖父的公寓,房子很大,但是我们是个大家庭,所以还是相当拥挤。但是在巴黎我们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当然啦,一切都由我的哥哥们带头!打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反叛。父亲因为是家族糖厂的负责人,必需留守塔美芮斯,但是那是在一个不同的区域--所谓的「禁区」(the interdite zone)里。因为法国极北的地带是很富庶的工业区,德国决定把它列入版图。母亲和我们一起住在巴黎,她得要有特殊的许可证才能到塔美芮斯探望我父亲。一九四二年开始,事情变得比较容易--我记得那一年我第一次回到塔美芮斯度假。在那以前,我们是不能回去的。
父亲不在身旁的事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对哥哥、弟弟也是一样。今天只要开两个钟头的车就到了,但是在当时可真是趟大旅程。由于几乎不受什么限制,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在耶稣会学校读书时--我大概是九岁、十岁左右吧,他们下午会放我们出来卖贝当元帅(Marshal Petain)的明信片,有时到店里卖,有时在街上卖给行人,有时是为了给红十字会筹款,有时是为了其它事情。在《好奇心》开头时,我做了一小段这样的描述。我记得蛮喜欢那样做的,因为他们下午三点以后就会放我们自由活动了。
学校生活
战争以后你继续念大学,然后念IDHEC;这其中哪一个比较重要?在Sorbonne(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或在电影学校的学习?
由于父母非常反对我的职业志趣,我们做过一连串的妥协。我比一般小孩提早一年完成高中学业,那时我还不满十七岁。然后他们帮我注册修习一些专为准备法国名校--the grandes ecoles"--入学考试而设的课程。如果你能进入其中的一个学校,你这一辈子就不用愁了,因为你就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分子。我想办法绝对要落第。在一门考试里,我刻意留了几页空白页,因为我害怕会在违反自己的意愿下被「那些」学校录取。最后我如愿地进入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因为我对历史及政治学感兴趣。第一年结束时,我争取到IDHEC的一个名额--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处处被接受的本事,虽然不见得够资格。我告诉父母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这学校是巴黎大学的一部分。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会念完政治学院,但同时也上电影学校。」他们同意了。念完政治学院第二年的课程后,我就放弃了;但是在IDHEC待了一年以后,我也觉得学不到什么。第二年念到一半时,我就被寇斯托雇用了。那时我二十岁。
IDHEC的教学什么地方让你不满?是不是太理论化了?
他们是非常理论化,大部分电影学校都有这个问题。对我而言,电影学校只有两种用处。第一种是:尽可能地看影片、试着去了解电影的历史、去了解你仰慕的人的创作过程并且审视他们的作品。第二种是:实习,那就是有机会去操作摄影机或剪接。当时学校非常穷,电影史的部分很不错,我们常待在电影资料馆里。但是有很多电影制作理论的课,而且是由平庸的老师教的,因此我很快就觉得那是无关痛痒的。所以,我并没有修完IDHEC的课程。
你在那里拍了一部片子,不是吗?
片子只有五分钟长。每个学生都制作了一部五分钟长的影片。IDHEC几乎没什么钱,所以我们用负片拍--然后直接在负片上剪接--剪接完了以后才把底片冲洗出来。这样说来,我算是拍了一部影片。
题材是什么?
那是受到贝克特(Samuel Beckett)及尤斯柯(Eugene Ionesco)早期作品相当影响的。那时候「荒谬剧场」(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已经开始在巴黎成形,但是还没有组织,也还没成功。《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在左岸(Left Bank)的一家小剧场首演时,我还在IDHEC。演出的评论并不是很好。我记得看过尤斯柯早期精采的作品--《TheLesson》及其它独幕剧。我跟一些和他共事的演员及导演很熟。我的影片是和《秃头女高音》(La Cantatrice Chauve;The Bald-Headed Prima Donna)中的两个演员拍的。故事是关于一些人在一个房间里等待一个最后失约的人。我想影片是在《等待果陀》正式搬上舞台两、三个月前拍的。所以,它和当时的气氛(mood)相当吻合。
许多和你同时代的人联合起来,成为推动电影杂志的影评人。你和IDHEC的同辈有没有发展出长期的友谊?
嗯--我这一辈的人在当年有各种不同的事和活动,虽然当时《电影笔记》才刚起步,楚浮或希维特(Jacques Rivette)一类的人也几乎还不存在。我记得见过夏布洛,那时他在国会的新闻室工作。我在IDHEC的班上,出了亚伦·卡维黎尔(Alain Cavalier)、米歇·密特朗尼(Michel Mitrani)以及成为设计师的皮耶·杰佛洛依(Pierre Geoffroy)。我大部分同学最后都当了电视导演。有一阵子常常见到杰克·德米,他那时正在拍一些短片--但是IDHEC并没有接受他的入学申请。
你是以什么样的资格及条件说服寇斯托雇用你到「卡利索号」上工作?
因为我会游泳!那是非常基本的条件。寇斯托有一个单人摄影工作队--贾克·厄尔多特(Jacques Ertaud)。后来我把他推荐给布烈松,在《死囚逃生记》中饰演一个角色。那时候他快要结婚了,所以寇斯托非常紧张。他试用了「卡利索号」上其它两个摄影师,但是我不认为他很信任他们,我一直不了解为什么。但是他到IDHEC去见院长,问他说:「你有没有一个有兴趣在暑假工作的学生?」基于某种理由,我被选为班长,所以我是班上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我当场就说:「我去!」接着,为了表示大公无私,我还是问了其它同学要不要去,但是他们对纪录片都不感兴趣。他们希望能够和尚·雷诺(Jean Renoir)、布烈松或贾克·贝克(Jaques Becker)一起工作。所以,我回到院长那儿说:「我想我是唯一的一个!」我决定冒个险试试我的运气。然后我就和寇斯托见面。我一点基础都没有,但是我假装我有一些剪接及摄影方面的知识--事实上我是懂一点摄影,因为我已经用我父亲的8厘米机器拍了许多影片,所以我的实际经验比我IDHEC的朋友多,他们想要当导演,而且只想当导演,他们对摄影机或摄影技术并不感兴趣。他们的角度是相当知识性的。
因此,我到马赛(Marseilles)去,登上「卡利索」号,学习潜水以及如何在水底使用摄影机。夏天快过完时,寇斯托知道他的左右手真的要结婚了,其它的人又不是很能干,于是他要求我留下来。当时我快二十一岁了,那可是一个大决定,因为我应该回IDHEC去。但是,我说:「当然!」接着,他就说:「那--导演、摄影、剪接都交给你管了!」我什么都不懂--不,也许懂一点吧,但是只有一点点。那是很重的责任。很幸运的,在第一年里我有时间去适应例行工作。然后我们就开始拍摄《沉默的世界》。我得说,当我踏上「卡利索」号,到达希腊的那一刻,我真的就想留下来。第一,因为我认为那是入门电影制作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做!第二,我对这种生活、这种电影制作由衷地感到兴趣。
沉默的世界
在印度洋、地中海及红海观察海底世界的经验,是否改变你对生命及宇宙的看法或看事情的角度?当《沉默的世界》上映以后,侯麦(Eric Rohmer)及巴赞(Andre Bazin)从存在论或本体论的立场提出一些颇受注意的声明,他们说这部影片打开了经验的新境界。当你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你有什么感觉?
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经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也很骄傲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那种感觉和最初几位航天员感觉到的一定很接近。但是,尽管我很佩服他(寇斯托)所发明的技术以及把这个新世界带给电影观众的魄力,尽管他是绝顶聪明、极富创造力、又很有幽默感--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很佩服他--但是,我们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当你年轻气盛的时候,你对你认为对的事情很执着。当年我受布烈松的影响很大,其实到今天还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在剪接时和寇斯托谈论到音乐,我跟他说:「你现在在做的,不是纪录片,是演艺事业。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快变成华特·狄斯耐(Walt Disney)了!」华特·狄斯耐那几年正在做所谓的「真实生活冒险记」(True-Life Adventure)的纪录片,和音乐紧密地剪接在一起,企图哗众取宠,如果我现在听到自己当年那番「严正」的话,我会觉得很好笑。
但是当时我很清楚我们做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从某一个观点来看,你常常是自己影片的第一位观众;当我看到我们所拍摄的种种时,不禁感到一阵惊叹。我们必需发明法则--因为太新进了,没有参考资料可循。由于我们是在水底,摄影机自然有一种移动性及流动性。如果是在陆上作业的话,我们不晓得要动用多少繁复的吊车及滑车技巧,才能拍摄出那样的画面。但是因为摄影机变成潜水员行动的一部分,我们像呼吸一样轻松地做到了。我不赞同寇斯托的地方在于出了水面之后,他的直觉反应比较偏向传统的奇观。我宁愿把它保留成为一种比较独特的经验。
你刚刚谈到和寇斯托不同的地方,你是否对那些现在使这个计划显得落伍的因素感到不满?--影片不真实的戏剧导向以及刻意的对白,那也许很适用于原始资料,但是用在这里使人怀疑所呈现的视觉经验。
正是如此。
譬如说,有一个潜水员正处在很危险的情况中,画面却忽然转接到甲板上的处理作业。很显然的,这绝对不会是原来的摄影流程。
寇斯托拍了许多优美的水底短片,在各种影展里得了不少奖。那些短片真的是关于珊瑚礁旁海底生物的精采报导(reportage)。但是,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我认为它应该保持绝对的纯真,而不要用现代那些所谓的「写实戏剧」(docu-drama)的技巧。我记得拍摄那段潜水员因为得了潜水症而在水底昏过去的画面的情形。当我们进入剪接室以后,寇斯托觉得需要加强效果,也要插入一段解释,我觉得这实在是有些过于教条化。我常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这显然是寇斯托的影片。
评述里的一句台词--「一座电影剧场,在海底下一千丈畲」--那是你或是寇斯托想出来的?
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将近四十年前我就发现寇斯托最令人猜想不到的倾向--他对剧情片的企图。去年夏天,当我们谈论未来有些什么可以合作的项目时,我就为了这一点和他起了争执。他认为我们应该做剧情片,他说:「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做剧情片,你可以帮我。」我说:「可是我没兴趣跟你一起拍剧情片。」当时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争论是因为他对如何超越纪录片的范畴这件事很关切。当我自己拍摄纪录片时,我认为我拍的是极端的纪录片,所谓「直接电影」(cinemadirect)的极端。但是,寇斯托总忍不住要加点戏剧色彩--甚至他的电视影片也含有「惊湛」的影像,可是我不喜欢它们被戏剧化的方式。
在这部影片里有一幕是:一只狗在甲板上对着一只活生生的龙虾直吠。有些人可能以为这是你惯有的幽默感。这是你目击而且希望保留的吗?
我不以为那是我的。那时候我对电影制作的看法非常「布烈松」、非常朴实。但是寇斯托总是不断地在寻找「人情味」。当时是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资助他的;在他们的杂志上及影片里,他们都很注重人类的角色。我记得工作人员在遇见鲸鱼后开始杀鲨鱼的那一幕。那是在印度洋里,一条幼小的鲸鱼受伤了,几只巨大的鲨鱼突然来到,并且开始吃小鲸鱼。这其实是水手与鲨鱼敌对的遗传性反应--水手痛恨鲨鱼。但是这点在影片里显得很可爱。
一九五六年,你随着《沉默的世界》去坎城,你和这位国家英雄分享「共同导演」的头衔,这部影片又正在角逐奖项。那必定是相当不同凡响的一次经验?
那时我二十三岁,竟然在坎城亮相!寇斯托来了几天后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多看看?」对我而言,发现电影世界是再好玩不过了!因为我已经当了几年的海底摄影师,在巴黎时也总是在剪接。我待了十天之后就回到巴黎,因为贾克·大地要我当《我的舅舅》(Mon oncle)的第二摄影师。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实现。虽然我的履历里常提到我当过贾克·大地的摄影师,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当过。回到巴黎后,很意外地接到一通坎城打来的电话,他们说:「你们得了金棕榈奖,但是影片没有派人来领奖。」那完全是个意外。那个时候是下午,但是当年的飞机不像今天那么方便。我甚至不记得后来到底有没有人上台领奖。后来我们发现评审委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执,一度无法达成协议。本来应该得奖的是柏格曼(Ingmar Bergman)早期的一部好电影--《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但是经过妥协之后,他们把奖给《沉默的世界》。当然,我们因此受到相当的注意,影片的票房卖座也非常得好!
我并不太在乎那些,因为坎城影展以后我立刻就开始和布烈松一起工作。接着,我受邀到美国,那是我第一次到那儿访问,为的是拍摄刚把「南塔克特岛号」(Nantucket)轮船撞沉的意大利轮船「安德莉亚·杜利亚号」(Andrea Doria)。所以,那是一个很忙碌的夏天。但是我已经在想如何利用《沉默的世界》带给我的好运,尝试去拍我的第一部剧情片。一九五六年秋天冬天,我写了一部自传性的剧本--一个发生在Sorbonne的爱情故事。修饰过了以后,我到处拿给制片人看,但是处处被拒绝。那是「新浪潮」之前的事,如果再隔个两年,他们应该会立刻采用,因为那是新浪潮的东西。但是在那个年头,一个从来没有导演过剧情片的人想要拍一部个人性的电影,是无法得到财务支持的机会的。
接着,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的朋友亚伦·卡维黎尔在火车站的报摊上买了一本叫《死刑台与电梯》(Ascenseu pour l’echafaud)的书,读完以后,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这本小说的情节和计谋真的很有意思。这可能可以开『黑色电影』(film noir)的先锋。」当时「警察电影」(film policier)类型在法国已经很受欢迎。我去见尚·杜利尔,他是布烈松的电影《死囚逃生记》的制作人。我告诉他:「读读这本书,我可以改编它。」这本书颇令人兴奋,因为它是一本很好的悬疑小说。他说:「好!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演员阵容,并且推销给片商。」我选择和我仰慕的作家罗杰·尼麦尔(Roger Nimier)--一位年轻的小说家--合作。
死刑台与电梯
是的,但是这是后来才明显化的,尤其是到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那时知识分子必须选择立场。尼麦尔是个多面性的人物,他是个杰出的文体论者、文学评论家,也是个非常老练的辩论家。他反对战后在法国揽权的左派分子,你知道,就是追随沙特(Sartre)及卡谬(Albert Camus)的那人。你可以说他的小说比较属于史汤达尔(Stendahl)那一型,但是比较轻快,也比较滑稽。我最近重读了他的《蓝色轻骑兵》,那实在是一本好书。他在加利玛(Gallimard)出版公司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那儿有一间办公室,也担任编辑的职位。他读了《死刑台与电梯》后说:「这是一本愚蠢的书。」「可是情节相当不错。」他又说:「好!但是我们必需整个改写。」打从一开始,我们就等于重新创造了影片中珍妮·摩露(Jeanne Moreau)饰演的角色--这可能是观众至今仍然和这部影片联想在一起的角色。她在书里几乎不存在。仔细想想,她对情节的发展似乎并不重要,只是在巴黎游荡,企图寻找她的情夫。但是在结尾时,我们把她变成阴谋的一部分。一旦我们开始改编的工作,事情进展得很快,我们签下了珍妮·摩露。现在大家常说:「你发掘了珍妮·摩露!」我并没有!她那时已经是位明星了,B级电影明星。此外,她也是那个时代重要的舞台剧女演员。她曾经在声誉良好的戏剧公司Comedie Franaise待过,也和杰哈·菲利浦(Gerard Philipe)共事过。但是除了和尚·嘉宾(Jean Gabin)合作的B级悬疑片以外,她在影片里的表现并不出色,她饰演的角色都不是很有意思的。可是,她有票房号召力。事实上,片商坚持要我们请珍妮·摩露。
这部电影对她在六年代塑造《夏日之恋》(Jules et Jim)及《夜》(La Notte)里的偶像级角色有帮助。
一点也不错。突然之间,他们发现她有成为大牌电影明星的潜力。在那以前,大家总认为她虽然是个好演员,也很性感,但是就是不上镜头。从早期梅尔维尔(Jeau-PierreMelville)的电影--例如《大赌徒鲍伯》(Bob le flambeur)--以及其它「新浪潮」时代的影片--我结识了杰出的摄影师亨利·迪凯(Henri Decae)。他帮助我、夏布洛、楚浮以及其它好多人拍摄我们的第一部电影。但是,我是同辈当中,第一个和他合作的。开工之后,珍妮·摩露最初的几个景是在Champs Elysees的街道上拍的。我们把摄影机放在手推车上,没有为她打光。当然啦,那是黑白片,我们用的是新上市的快速影片Tri-X。比较严谨的电影制作者认为那种影片的粒子太粗了。我们拍了好几个珍妮·摩露的推轨长镜头。当然,影片结束时有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
精采的音乐,加上她的声音--她发自内心的声音。打在她身上的光全部都来自Champs Elysees闹区的橱窗。当时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照常理推断,摄影师应该会强迫她上一大堆的妆,因为据说她的脸并不上镜头。
第一个星期,冲印厂的技术人员在看完冲片之后,闹起革命来了。他们去找制作人,说道:「你绝对不可以让马卢及迪凯毁了珍妮·摩露!」他们简直被吓坏了。但是当《死刑台与电梯》上映时,珍妮·摩露的一些重要特质猛然跳跃在银幕上:她可以看起来几乎是丑陋的,但是十秒钟之后,像换了张脸一样,变得无比地迷人。可是,她只是在表现她本来的面目。这个特质在《孽恋》里再度得到肯定,这部片子我几乎是马上就接下来拍的。所以,我对塑造她成为明星的事情是有点贡献,但是她那时已经拍了七、八部电影了。
除了创造性的摄影之外,你在结构上也冒了相当大的险。就像在《双重保险》(Double Indemnity)里,佛烈德·麦克摩瑞(Fred Mac Murray)及芭芭拉·史丹妃(BarbaraStanwyck)几乎从来没有碰面。这两个情侣,我们在谋杀发生之前刚刚看到他们,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是在一起的。接着,摄影机拉回来,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她在电话亭里。他们从来没有碰过面,他们从来没有被看到在一起。直到影片的最后一秒,一张照片才成为把他们送入监狱的最终证据。你有没有担心过这可能会疏离观众?还是你真的期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制造一种绝对的冷冽感?
就像刚才说的,珍妮·摩露的角色在原书里并不重要,她只是个在开场时被杀害的那个男人的妻子。这本书--以及这部影片--是关于一个男人犯下了天衣无缝的谋杀案,却很愚昧地困在大楼的电梯里。两个孩子偷了他的车,去到巴黎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在那里杀了人。所有的证据都指出他做了这件旅馆谋杀案,但是,事实上他当时……嗯,这就是关键所在,这就是这本书的噱头。在剧本里,我们扩展他的爱情事件的情节。我们不想把它当做是一部关于两件谋杀案的电影。就像别人利用他的车子、他的手枪行凶一样,我们觉得如果他计划在做案后立即去和一个女人会面,她到处在找他,但是他们从来没碰到面,这部影片会变得比较有趣。我们从来没想到说这是一种大胆的做法,真的!
我记得,在编剧本的时候,我们考虑过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在某个时候会个面,当时我们相当犹豫,最后我们决定不要让他们会面,只有在最后结尾的部分,当她被逮捕的时候,才出现这场景--全片最好的景之一。摄影师正在冲洗相片,在水中的放大影像里,她看到他们俩人在恋爱中;就这样,他们重聚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一起。对我们来说,那似乎非常浪漫!
有几个你后来的影片里有的主题、情况及角色都在这里面出现了。爵士乐的应用、随机突发的暴力(汽车旅馆里的杀戮看起来很像《大西洋城》的前奏)、人所受限的命运、你利用政治背景的手法(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后盾)、当事人所执迷的生活、自杀等等。你自己是不是也看到这一点?你对这部影片带有这些特征是不是感到惊讶?因为你原来是把它当做是一部冷漠、超然的悬疑片来拍的。
拍《死刑台与电梯》时,我是刻意选择以这本书--一本悬疑类的书--来做开端。我晓得我必须拍一部能够以B级电影促销的影片。当然,我是相当有野心的。虽然别人推荐几位剧作家给我,我和罗杰·尼麦尔合作;选择和当时很受尊重的作家共事的这个事实,表示我对这个计划有很大的野心。但是,如果一切能按照我的意思做,我宁可拍比较自传性的。其实,如果三年后我就拍我的第一部剧情片,我可能可以真的这样做。现在再看《死刑台与电梯》,我发现我很巧妙地注入几个也许是下意识中跟我很亲近、在我往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我们已经有了情节,但是情节只是个骨架。我一心想拍一部好的悬疑片。很讽刺的是,当时我非常崇拜布烈松,但是又有想拍一部类似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的欲望。《死刑台与电梯》的情节有适合用前者风格的,也有适合用后者的。在好几幕里,尤其是在电梯里,我企图模仿布烈松。
逃离电梯就好象《死囚逃生记》里逃离监狱。
是的,一点也不错。但是那是很自觉性的。虽然有点讽刺,但是我同时也在模仿希区考克制造悬疑效果的手法。那种紧张不安、那种出乎意外。当然,如果不谈那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因而含有许多笨拙的痕迹,在风格上我比较接近布烈松。所以,我被分化了。除此之外,透过小孩子的角色(当时他们被称为blousons noirs--「穿黑色皮夹克的阿飞」,因为这些来自郊区的小孩都穿黑色的皮夹克)来描绘新的一代,以及新的巴黎。传统上,法国电影所表现的巴黎总是以何内·克莱(Rene Clair)做象征。我刻意地把巴黎最早的几栋现代建筑物摄入镜头。我f造了汽车旅馆--当时全法国只有一家汽车旅馆,但是并不在巴黎附近,所以我们得跑到诺曼底(Normandy)去拍。我所展露的巴黎--虽然不是未来派的,但是至少是一个现代城市--是一个已经有些失掉人性的世界。我没有意识到拍摄《死刑台与电梯》是在做一件个人化的事情。我几乎把它看做是一种练习。《地下铁的莎芝》也是一样。当时我并不晓得《地下铁的莎芝》的主题含有某种在我往后作品里极为重要的观点:小孩子因为发掘成人的世界而接触到腐败。显然,这是昆诺的世界,我把它接收过来;我不知道那其实也是我的世界。
我想把话题再转回到布烈松。你要的是什么?--你觉得拍纪录片只是当半个学徒,你想要和一位剧情片导演一起工作吗?
我从来不想当助理导演。和寇斯托在一起,我从技术人员开始,然后是摄影师、剪接师、音效人员。我没有意思要回巴黎追求助理导演的生涯。和布烈松一起工作的唯一理由是我仰慕他。我把他放在很崇高的地位上,比其它任何法国导演都崇高。我也很景仰雷诺,但是雷诺那时候不在法国工作。我很幸运地透过一个朋友和布烈松见面。他喜欢《沉默的世界》,因而对这位非常年轻的男士感到兴趣,就说:「你为什么不来跟我一起工作?」那是再好不过了!我不认为我会和何内·克莱曼(Rene Clement)一起工作。我并不是要批评他,我只是很仰慕布烈松,坚信他的方法是拍电影唯一的方法。现在我的想法已经改变了,但是在那些年里我对这点非常执着。
路易·马勒 - 关于《再见,孩子们》
《再见,孩子们》是法国导演路易·马勒根据自己童年经历改编而成的故事,是这位被受争议的导演关于自己苦难童年的回忆。其实与其说是马勒自己的童年回忆,不如说是生存在那个年代的一代法国孩子共同的苦难童年的回忆。路易·马勒这位新浪潮时期出现的著名导演一直以来都以拍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边缘题材闻名。而也是因为他这种一贯的大胆尝试的风格,才让他的电影生涯充满了艰辛与责难。他于1971年拍摄的《好奇心》直面地表现了母子乱伦这一极其敏感的题材,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也因为国内巨大的压力离开了法国。而当他回到法国并于1975年拍摄了反映德国占领法国时期的青年法奸的影片《拉孔布·吕西安》时,起初外界对影片的赞扬没多久就转变成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原因是法国人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用正面笔触去描写的全无道德感可言的法奸形象。其实与其说是他们无法接受吕西安,还不如说是他们无法接受影片如此真实直接地揭了法国人的疮疤。其实马勒只是想通过影片表达出这个青年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的迷惘与青春的残酷,只不过他的这个人物却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法国人随波逐流的状况。但国人就是无法理解与原谅马勒,他们将马勒骂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而马勒这一走就是整整十二年。而在1987年,路易·马勒终于又回来了,这次他带回来了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影片《再见,孩子们》。这部真挚感人的影片真实地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展现在观众眼前,他们被深深地打动了,法国人终于原谅了马勒。这部影片不但在当年的法国最高奖凯撒奖上席卷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7项大奖,还在同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为法国捧回了又一座金狮,这也宣告了路易·马勒这位饱受争议的电影大师的回归。
影片的故事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朱利安与波奈特之间关系变化的过程,两人从起初的朱利安同其他人一样欺负波奈特,到通过了解朱利安发现波奈特与自己一样喜欢文学和音乐,从而开始与他交往,再到“寻宝”发生的那次意外为转折点,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友好。直到两人成为挚友后,波奈特被盖世太保带走结束。这整个的过程与其说是两个孩子关系从对立到亲密的过程,不如说是两种文化、两种不同信仰相互接受的过程。朱利安是法国传统的天主教徒,而波奈特是犹太人,是所谓的“异教徒”(虽然他自称是“新教徒”,但对于保守的天主教来说,那同样是“异教徒”)。朱利安所代表的天主教正统与波奈特所代表的犹太民族的信仰上的差异与对立,不但反映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也反映出为什么纳粹如此仇恨犹太人,他们不过是嫉妒和害怕犹太民族的聪明,因此为了维护正统而要消灭敌人。然而任何不同的文化与信仰间必然有相同的东西,两个孩子在找到了这些共通之后终于逐渐彼此接受相容。其实这种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包容不单体现在两个孩子的关系上,在以校长所代表的正统天主教传教士身上也得到了体现。他们不但冒死收留了这几个异教的孩子,而且还尊重他们的信仰。这点在波奈特知道自己身份被朱利安怀疑后主动接受基督教传统的“圣餐”时,校长却拒绝给他并帮他掩盖过去(其实也有出于对异教的恐惧的原因)可以看出。而校长冒死收留保护这几个孩子则真正体现出在人道主义面前,在上帝的博爱面前,一切都没有保护无辜生命更为重要,而校长也终究因此献出了生命。马勒以此劝谏人们抛弃偏见,用博爱去与人相处,达到真正的与上帝的和谐。
影片中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含义。
它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或者一个庇护所一般。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不管外界发生的腥风血雨,他们可以自由地玩耍,他们之间的快乐与悲伤,争斗与相容都在主的庇护下,使得他们可以健康的成长。倘若不是不时发生的盟军反攻的轰炸和盖世太保的例行检查,他们几乎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然而,战争的的确确是存在着的,它存在于那轰炸声中,存在于例行检查中,存在于宵禁令中,存在于老师的局势图中,存在于朱利安许久未见的父亲和波奈特集中营的父亲和失散的母亲,存在于每个法国人的心中。这罪恶的战争摧毁的不单是人的生命,也摧毁了人的整个精神世界。从二战后欧洲的混乱中(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我们都可以感觉出。可在这座充满了主的庇护与爱的乐园中,孩子们的心灵尚保有一片净土。然而学校的被迫关闭和校长以及波奈特等三名犹太学生的被捕终于摧毁了这一切。
所以朱利安才会在回忆的独白中说道:“已经过去了40年,但我至死都会记得那个1月早晨的每一秒钟。”这个早晨的每一秒钟都见证了那段痛苦的记忆,见证了那个苦难的时代,也见证了朱利安(马勒)的成熟。
而校长最后的那句:“再见,孩子们。”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祈祷。他祈求上帝能保佑这些苦难的孩子们安然渡过童年,忘却那些忧伤与泪水,同时它又是一种希望,希望孩子们能以一种宽大博爱的胸怀去面对人生。而这些希望从校长每每传教时的谆谆教诲,以及以他为首的传教士们不对纳粹妥协,哪怕是被抓走时,校长仍高昂着头颅保持着尊严,以及后来学校终于重新开学都可以感觉出。
其实在影片中,路易·马勒并没有放弃他一贯关注的边缘题材,他只是在一个能被主流所接受的故事框架下用大量的细节去表现那些东西。他用隐喻的手法表现了性的觉醒与暗示性的表现了乱伦关系。这以朱利安在澡盆中洗澡一段最为明显和出彩。水属阴性,象征着女性,而当时的朱利安泡在水中想念母亲,并且他以一种近乎是性欲得到满足后的状态享受地潜入了水中。还有他对波奈特说他十分喜欢做着春梦尿床后睡在水上的感觉,影片在拍摄他第一次尿床的戏时他在梦中时脸上的表情有着明显的快感。而他与母亲的关系也带有或多或少的乱伦味道(虽然可能从未发生过)。这从朱利安哥哥对母亲的憎恨(虽然不是很明显),他曾对朱利安说:“你才是母亲的宠儿。”(表现出明显的嫉妒)以及母子间过分亲密的关系(对比母亲与哥哥的冷漠)都可以感觉出些许的不寻常。而在另一个方面,让马勒最饱受责难的法奸又再次出现在影片中。同样是迷惘而无道德感可言而最终出卖了自己人的青年,只不过因为这个杂工被放在了游离于主线之外的从属位置,并且在对于其道德感的描写并为着太多的笔墨,所以对观众的情感冲击不是十分明显和强烈(当然是相对于吕西安来说)。而影片同时还表现了带有一定正面色彩的德国军人(餐馆那场戏,那个德国军官训斥为难犹太老人的法奸),以及随波逐流的出卖自己人的修女(正是他出卖了躲在病床上的犹太孩子)。这些都表现了马勒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真诚。所以无论是乱伦还是法奸都只是马勒遵从于自己内心对青年时期的迷惘与道德矛盾的表现罢了,他并未刻意影射什么。值得一提的是这回他以这样一个主流的故事附带了他原先遭受批评的元素却为法国的主流文化所接受,这不得不说是马勒对那些指责他的人们的一次绝妙回击。
路易·马勒不同于新浪潮时期的其他导演。他们大多都喜欢在影片中使用各种复杂的摄影技术,用大量复杂的蒙太奇声画剪辑去表达思想,用高难度的长镜头推轨去实现空间的连贯,而不是很注重完整连贯的剧情。马勒则与他们不同,他似乎更重视剧情,关注剧中的人物命运。而在本片中,他以一种冷色调成功地营造出了那个冰冷而绝望的年代,他那几乎不让观众察觉摄影机存在的拍摄手法,让观众将全部的注意力和感情投入到故事当中(这点与其他新浪潮导演最为不同,他们大都是让观众在一种疏离感中去思考影像之外的一些东西)。马勒以一种平实质朴,却又不失优雅的镜头语言将这个关于童年记忆的故事娓娓道来。它就像一首诗,优雅而伤感,却沁人心脾,使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