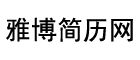马丁?布伯的个人简介
马丁布伯(1878――1965)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之一,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晚年移居在以色列。他以关系为世界的本质。这一观点在心理治疗中,可以很好的帮助理解来访者生命的认识基础。心理疗法中...生平
马丁布伯(1878――1965)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之一,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晚年移居在以色列。他以关系为世界的本质。这一观点在心理治疗中,可以很好的帮助理解来访者生命的认识基础。心理疗法中,受到他思想影响的大师很多。包括心理剧创始人莫雷诺、以来访者为中心疗法创始人罗杰斯、完形疗法创始人皮尔斯等等,他们的疗法本质上都是在实践马丁布伯的哲学。代表作有《我与你》等.
布伯于1878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1896年至1900年,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来比锡大学、柏林大学与苏黎世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艺术,醉心于狄尔泰和齐美尔的哲学。他早年积极参与犹太复国运动,1901年出任该运动的主要杂志《世界》的主编。1916年,布伯有创办了德国犹太人月刊《犹太人》。这份杂志从诞生之日起迄1924年停刊为止,一直是德国犹太人享有最高声誉的喉舌。1924年至1933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宗教哲学教授与伦理学教授。希特勒上台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纳粹主义与振兴德国犹太人精神力量的工作中,成为犹太人的精神领袖。1938年,布伯移居到巴勒斯坦,任希伯来大学宗教社会学教授,而后又出任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是以色列科学与人文学院的首届主席。1965年,他逝世于耶路撒冷。
布伯一生的活动集中在四个领域内:(1)宗教哲学。在《我与你》(1923)及其续篇《人与人之间》(1947)中,他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关系”哲学。其他的主要哲学著述是:《两种类型的信仰》(1950),《善恶观念》(1952)。(2)《圣经》翻译及有关论著。1925年,布伯和罗森茨威格一起着手把《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德文,罗森茨威格去世后,由布伯独立进行并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工作(1962)。(3)对哈西德派的研究。哈西德派是十八世纪中叶波兰犹太人中出现的宗教神秘主义团体,十九世纪中叶其教徒已占东欧犹太人的半数。该派反对犹太教的正统律法与拉比的误伤权威,强调通过狂热的祈祷与虔信(希伯来文Hasid意为“虔信者”)与神结合。其教义对于布伯思想的形成关系甚大。他在这一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哈西德遗事》(1927)、《哈西德派与人的道路》(1958)、《通向乌托邦之路》(1947)。(4)参与犹太复国运动。
这些表面看来互不相关的活动却有着共同的基础,即他以“我―你”关系为枢机的“相遇”哲学。
布伯的圣经译文具有一种相当奇异的风格,文辞晦涩幽眇,奥博艰深。但这并非是顾弄玄虚,其间自有一番良苦用心。按照他的说法,《圣经》不是可随便读的,人理当“苦习”它。优秀的译文只能为那些希望进行这种艰苦努力的人服务。翻译乃是勉励探求作者的真精神,是译者(及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以其本心体悟作者的本心,视作者为导师先贤,奉作者为“你”。其间自然不难觅见狄尔泰对布伯的影响,但此说的根本核心正是他毕生对人类所倾注的热切冀望――把全部生命投入到与其他在者的相遇之中。
这也可以解释他何以对哈西德派如此推崇备至。在该派教义的启迪下,他意识到宗教不过是人与上帝及先知圣徒的亲切“对话”,其间务需任何由概念体系构成的神学作为中介。沿循这条思路,他打破了宗教之间的隔阂,从《旧约》进入《新约》,潜心聆听耶稣的山训与《约翰福音》的启示,故尔他的学说不再被视为犹太教中某一异端的代表,而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所珍视的财富(《基督教名誉录第二卷,我与你》)。
依据其“相遇”哲学,布伯给犹太复国运动注入了全新的精神。他满怀激情地向犹太人呼吁,切不可把阿拉伯人当作仇敌,当作利用、仇杀的对象,要与他们建立相遇关系,让两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意味深长的是,1965年布伯去世时,阿拉伯学生联盟竟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他的葬礼,向这位犹太人思想家志哀!
《我与你》
《我与你》是布伯最重要的著述。
全书共分为三卷。第一卷旨在挑明世界的二重性与人生的二重性,“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对立,“我―你”与“我―它”人生的对立。第二卷讨论“我―你”与“我―它”在人类历史及文化中的呈现。第三卷展示了“永恒之你”即上帝与人的关系。
人置身于二重世界之中,因之他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人筑居于“它”之世界。这意思是:为了自我生存及需要,人必得把他周围的在者――其他人,生灵万物――都当作与“我”相分离的对象,与我相对立的客体,通过对他们的经验而获致关于他们的知识,再假手知识以使其为我所用。只要我执持此种态度,则在者于我便是“它”,世界于我便是“它”之世界。这自然会招致两种后果。首先,与我产生关联的一切在者都沦为了我经验、利用的对象,是我满足我之利益、需要、欲求的工具。布伯将这称之为“我――它”关联。其次,为了实现利用在者的目的,我必得把在者放入时空框架与因果序列中,将其作为物中之一物加以把握。因为,如果我对对象之间的诸种联系及其时空网络中的位置无所认识,我如何能成功地利用他们?我对在者的态度,取决于我此时此地的需要,取决于他们的具体性状、素质。如此,则在者不过是众“它”中之一“它”,相辅相成的有限有待之物。
人也栖身于“你”之世界。在其间他与在者的“你”相遇,或者说,与作为“你”的在者相遇。此时,在这与我不复为与我相分离的对象。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1)当我与“你”相遇时,我不再是一经验物、利用物的主体,我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任何需要,哪怕是最高尚的需要(如所谓“爱的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因为,“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我当以我的整个存在,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真本自性来接近“你”,称述“你”。(2)当在者以“你”的面目呈现于我,他不复为时空世界中之一物,有限有待之物。此时,在者的“惟一性之伟力已整个地统摄了我”。“你”即是世界,其外无物存在,“你”无须仰仗他物,无须有待于他物。“你”即是绝对在者,我不可拿“你”与其他在者相比较,我不可冷静地分析“你”,认识“你”,因为这一切都意味着我把“你”置身于偶然性的操纵之下。对“我――你”关系而言,一切日常意义的因果必然性皆是偶然性,因为它匮乏超越宿命的先验的根。
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传达布伯学说的部分意蕴。当安徒生把一朵绯红的玫瑰奉献给旅店里那位奇丑无比的洗碗碟的小姑娘时(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夜行的驿车》),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屈尊俯就的怜悯之情。一切怜悯都是有待的,有待于他人的美与小姑娘的丑,有待于她地位的卑微,有待于她与其他对象的比较,一句话,有待于命运的偶然。但在这一刹那的“我”与“你”的相遇中,在者之间因偶然性而产生的差异顿然消失,她的丑陋、卑微不过是命运的任意捉弄,而“我”超越时间与宿命与她之“你”相遇。因为,尽管她不过是一有限有待的相对物,她的“你”却是超越这由冷酷无情的因果性所宰制的宇宙的绝对在者。此时此刻, “你”既是统摄万有的世界,而“我”以我全部的生命相遇“你”那备受煎熬、歧视的灵魂,“我”因“你”的每一痛苦,每一次欢乐而颤栗,“我”的整个存在都沉浸在“你”的绚烂光华中。
然而,在布伯看来,“我”与“你”的相遇,“我――你”之间的纯净关系既超越时间又羁留于时间,它仅是时间长河中永恒的一瞬。人注定要厮守在时间的无限绵延之中。因之,他不能不栖息于“你”之世界,又不可不时时返还“它”之世界,流连往返于“我――你”的惟一性与“我――它”的包容性之间。此种二重性便是人的真实处境。此是人生的悲哀,此也是人生的伟大。因为,尽管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留存在“它”之世界,但人对“你”的炽烈渴仰又使人不断地反抗它,超越它,正是这种反抗造就了人的精神、道德与艺术,正是它使人成其为人。“人呵,伫立在真理的一切庄严中且聆听这样的昭示:人无u2018它”不可存在,但仅靠u2018它u2019则生存者不复为人。”
超越:自失与自圣
布伯的学说直接针对着西方思想史上两种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其目的是力图阐释宗教哲学的核心概念――超越――的本真涵义,澄清基督教文化的根本精神――爱心。
在《我与你》第二卷结尾处,布伯把他所反对的两种超越观比喻为两幅世界图景:其一是用至大无外的永恒宇宙来吞没个人人生,让个体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宇宙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实现不朽;其二是用至大无外的“我”来吞没宇宙及其他在者,把居于无限时间流程中的宇宙当作“我”之自我完成的内容,由此铸成“我”之永恒。
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把前者称为“自失”说,把后者称为“自圣”之说。两者皆肇始于人对超越,或者说,对“获救人生”的追求。超越本于人对存在(自身的存在与宇宙的存在)之绝对偶然性与荒诞性的恐惧,对生存意义的反思。这种反思很自然地与某种更高目的相联系,因为,反思本身就意味着人反抗物性生存,它促使人超脱身内卑下的欲求,透破功名利禄的束缚,进抵不为形躯之我所圄的境界。所不同者乃是超越的指向,换句话说,反抗只是从消极方面表明了超越的性质,但超越本身具有何种价值内容,人于何处获得安身立命之所,却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由此便产生出“自失”说与“自圣”说之分。
自失说源远流长,它可谓是与人之反思同日而生的一种超越观。在柏拉图的理念中,斯多葛学派的禁欲主义,普罗丁的宇宙论,经院哲学体系,中世纪的神秘主义,黑格尔的宇宙理性中,我们处处皆窥见它的踪迹。为满足人对意义及不朽的渴慕,此学说将人置身于其间的宇宙本身加以圣化,神化,赋它以神妙莫测的动机,宣称在这浩瀚恢弘的宇宙秩序中隐匿着至善至美的目的。当人意识到个体的有限不过是宇宙进程之无限性中的一时一瞬,当人“自失”于此进程,则因人生无常而生的种种痛苦将在这庄严的无限性前自惭其渺小俗浅,自失指引人步入齐万物,等生死的超然灵境。然任何一种类型的自失说都难以避免一些具根本性的毛病。超越要求发端于对无意义的反抗,但自失说只是断定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宇宙秩序具有某种神圣的目的性,而对此目的或意义本身的内容却无所说。另一方面,它对道德哲学的影响简直是毁灭性的。如果宇宙的必然进程正是道德境界的展开过程,那么我们即在肯定一切皆是善的,一切皆是合理的。更糟的是,这种学说还暗含着这样一种观念,所有的个体都是宇宙进程实现自身内容的工具,如此,“爱心”便成为了毫无意义的呓语。
自圣说把超越的指向寄托在个体之自我完成之上,但它同样不能摆脱自失说的困境。因为,无论人的精神需要何等崇高,距离物欲和私情何等遥远,它终究是我的一种需要。故尔断言道德乃是某种需要的实现既是断言道德本为功利。近年来在欧美盛行一时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特别明显地暴露出这种学说的致命缺陷。例如,弗洛姆为了把以个体之自我完成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与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相调和,便干脆把利他境界也归结成自我实现的必要环节(弗洛姆《为自己的人》第一章)。但是,倘若自我牺牲的终极目的乃是自我满足,则此种牺牲已丧失了其本原性,丧失了其道德绝对性。
布伯在《我与你》第三卷里,把主张宗教超越既是沉入神我一体、天人合一出神入化状态的神秘主义作为自失说的代表,把断言宇宙万有皆寓于“我”体的大乘佛学作为自圣说的代表。在他看来,前者错把宇宙在时间中的无限绵延与无穷因果当作了价值论中的不朽,因之,可以说它是从对宇宙之无意义进行反抗开始,却以向后者俯首称臣而告终。自圣说同样没有看破其间的道理。“我”本身不可能领有价值之先验的根,否则我何需反思意义,追求意义。反抗只是超越的起点,而超越的完成只可存在于比我体更高的境界中。自圣说实则是妄图用时间的无垠来充实我体,因此它与自失说同出一辙。
如果价值或超越指向既不在人之外的宇宙中,又不存在于主体内,那么它可能栖于何处?此问题可指引我们进入布伯思想最微妙精深之处。他的回答是:价值呈现于关系,呈现于“我”与宇宙中其他在者的关系。关系乃精神性之家。蔽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种种学说皆滞留在表面世界,“它”之世界,惟有关系能把人引入崇高的神性世界,惟关系方具有神性,具有先验的根。当《圣经》昭示人要“爱上帝,爱他人”时,人不仅领承了通向神性世界的钥匙,且同时也领略了价值的本真内容。爱非是对象的属性,也非是“我”之情感心绪的流溢,它呈现于关系,在关系中敞亮自身。正是在这里,“我”与“你”同时升华了自己,超越了自己。人于对 “它”之世界的反抗中走向超越,人于关系中实现了超越!
关于马丁?布伯的若干笔记
■真正的心理分析医生与其病人的关系,它同样充分表明了相互性的标准局限性。如果他只是满足于“分析“病人,即从其心理世界中挖掘出无意识的要素,并把通过这种程序加以转变了的心理能投放到有意识的人生工作中去,那么,也许他的治疗会取得一定的成功,在最好的情况下,他能帮助心理紊乱无序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整合自己。但是他却无法完成自己 真正的任务――让萎缩的人格中心获得再生。
惟有这样的医生方能胜任此任务:他一深邃的眼光洞见到一患病心灵中潜伏的同意性,但若欲如此,医生必得与病人建立人格与人格间的伙伴关系,切不能把他当作观察、研究的对象。为了把这一统一性解放出来,为了让病人建立与世界的新和谐并实现其统一性,一生必须象教师一样,不仅仅拘泥与两极关系中的自己一方面,且同时要凭借“现时性”的力量站到另一极去,设身处地的体会治疗效果。同样,倘若病人竟然进行“总结”,站在医生的一极来体验效果,则这样的特定的“治疗”关系便不复存在。在人际关系中,即亲若兄弟,有落落寡合,惟此种人才可治疗他人,教育他人。。。。。。
如果在一种关系里,其中的一方要对另一方有目的、有计划地施加影响,则这种关系里的“我――你”态度所依据的乃是一种不完整的存在,一种注定了不可能至于完善的相互性。
――马丁。布伯
■[法]E.勒维纳/文 黄启祥/译
他人不是作为客体或对象向我显现,这个说法,并不只意味着我不把另一人作为我支配的一个东西、一个“某物”,而且还主张,在我自身与他者们(the others)、我与某人之间建立的原初关系不能被不恰当地说成是占有、把握和受制于客体的认知行为。这个被假定是外在的客体实际上已经被我包含了:因此内在和超越的含糊身份也已经被我包含了。与他者们的关系正是这种含糊性和唯心主义哲学的老传统的终结。在这种唯心主义老传统中,语言的出现只是一个辅助因素、一种手段,通过它使严格说来是发生在我们内部的事情让外人知晓,或者是作为一种服务于内在思想的分析工具,或者是作为一个积累内在思想所取得的成果的仓库而起作用。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这种内在性质马上就破裂开来,而语言[那在说着你(thou)的言说,即便只是隐含地]就不只是对于一个相遇 (meeting)的可有可无的陈述。它就是这个遭遇事件本身、这个在对话中来自自身的思想喷发,而远非理智的认知 (noesis)。这种认知以同样的方式将自身投向客体,而这客体就是它给予自己的。
马丁?布伯发现了这种喷发或者意向性向语言内部的转向。因此,他的哲学方法是从原初语词、根本语词和建基语词(Gnmdwort)开始的,而不是从对 “我思”的反思开始的。基本语词“我―你(I-Thou)”这个建基语词最终是开启所有语言的条件,甚至是叙述纯粹认识关系的语言的开启条件,这种认识关系是由建基语词“我―它(Ich―Es,I-That)”来表达的:对于我-它来说,正是由于它是语言,因而实际上也向一个对话者说话,所以已经是对话或者对话的残余了。
对于对―话关系及其现象学意义上的不可还原性的估价,对于这种对―话适合于建构一个意义秩序(这种秩序是独立存在的,并像传统的认识活动中享有特权的主体―客体相互关系一样是合法的)的特点的估价,这些将成为马丁?布伯哲学工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隐含于社会亲缘(proyannty)中的多样性,当它与统一性或者学问、科学所追求的综合性或整体性相比时,也已不再被看作是理性的退化或匮乏。它是一个具有充分意义的伦理关系秩序,也就是一种与不可同化的他者们、因此也可以被恰当地说成是与不可被作为对象把捉的(不可被把握、占有的)他者们所引发的他我性(alterity of the others)的关系。在布伯的声音使其自身被听到的过程中,无论是否达到了一致与和谐,但它对于这个秩序的完全原本状态的发现,对于其意义或“范畴”的详尽阐述,这些都是与这位思想家的名字分不开的。这些声音就像伽布里?马塞尔(Gabriel Marcel)在他的《形而上学日志》(Metaphysical Journal)中发出的声音一样充满权威性。一个人即使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他的行进和工作中,他的脚踏在其上的对话基础已经被另一个人开辟了,他也不会减少对于布伯的忠诚。没有什么能减少对于他的敬意。他者(the other)的他我性使得他或她不可还原为客体的客观性和存在者们的存在。对于这种他我性所做的任何反思都一定会看到布伯开辟的崭新视野,也一定会发现包含于其中的鼓励。
因此,尽管我在对布伯的评论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质疑他在《我与你》(I and thou)中所作的建基性的和极出色的分析,更不是要着手于一项去“改进”一位
真正创造者的学说的危险或可笑的计划。然而,布伯所开辟的沉思图景是如此丰富,至今还如此新颖,以至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使某种意义的视野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从那被开拓者指示出的小路的角度上,并不总被看到。
我的评论突出布伯的观点与我在一些随笔中表达的观点的区别,这些评论是关于多种主题的工作性的笔记。它们不提供那些使得它们可能的先行洞见,而是经常采取提问题而非异议的形式。在布伯的文本中,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甚至发现具有这些答案的观念之所在,也并非不可能。但是这就将涉及一项不同的研究了。
这里不妨给一个更为初步的评论。面对着如此多的被释放出的力量,面对着如此多的充满我们历史、我们社会和我们灵魂的粗暴贪婪的行为,(在布伯看来)我却应当转向我―你或者“一个人对他者的回应(responsibihty,责任)”,以发现大写的人的范畴,这也许会使一些人感到震惊。可能许多卓越的心灵也会有同样的震惊。我们已逝去的亲爱的朋友A.德?威尔汉斯教授(Alphonse de Waelhens)就正是这样(这本书中的好几处使我们回想起他)。在为现象学贡献了那么多的优秀著作之后,当他谈及使哲学人类学与真实的人类苦难面孔分离的距离时,当他为了亲自看到这种苦难而(在与图书馆打交道多年之后)开始频繁出入精神病医院时,他感到了这种震惊。也许,在伦理亲缘结构中探求人的秘密不等于对这种苦难视而不见。并非由于对进步(它以安慰性的辩证法或预示着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经验征兆为基础)的信心,这种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研究才被证明是合理的。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存在的不可缓和的必然性而不是关于他我性的伦理学才能说明这种非人的人类历史。但正是因为人类产生于存在内部,那些不变的必然性、那些粗暴的行为和那种普遍的偏见才被质疑,才被谴责为残酷、恐怖和犯罪。而人性既坚持于存在之中,同时又通过圣徒们和义人们宣称反对存在意向 (conatus essen- di);这种人性不仅要以(海德格尔讲的)“存在于世界之中(Lelng-in-the-world)”为基础,也要通过书籍或经书(books),以求得理解。在与他人的伦理关系的反自然的表现中,人类的人性不正是存在之作为存在(being qua being)的危机所在吗?
对于布伯来说,我(I)诉求的这个你(Thou),作为一个向我说着你的我(as an/who says thou to me),在这个吁请中被听到了。因此,对于我来说,我对你的吁请从一开始就是对一种交互性(reciprocity可逆性,对等性)、平等或公平状态的建立。由此而把我理解为我,由此而有了我充分的主位化(thematization,主题化)的可能性。一般说来,我的观念或我自身(Myself)的观念直接地来自于这个关系;于是,对我自身的总体反思才是可能的,我自身才可能被提升到概念层次,提升到那高于我的生活中心地位(centrality)的主体性。在传统的唯理论那里,这个提升被认为比中心地位“更好”或者“更有精神性”,它还被说成是从带有智力和道德幻觉的、偏狭的主体主义中“解放出来”。
在我自己的分析中,达到他者的原初途径,并不在于我向另一个人清楚地言说,而是我对他或她的回应(责任)。这是原始的伦理关系。这个回应被另一个人的面孔所引起、所造成,它被描述为对外貌显现的可塑形式的突破。这种突破意味着面对死亡的直接,以及要我不放弃他者(上帝之言)的命令。由于不依赖于世界语境所给予它的意义,面孔和它在被知觉中的原创性被赋予了方法论上的重要性。不能消除的我的中心地位(这个我不能离开其第
一人称)意味着对邻居的回应的无限性:我永远不能免除对他者们的尊重。对于另一个人的回应是这样一个回应,它既不被任何自由行为(这个回应是其结果) 所规定,也不为这种行为所衡量。这无缘无故的回应类似于人质的回应,它尽可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而不要求相互性或对等性。这就是博爱和为他人赎罪这些观念的基础。因而,与布伯的我―你相反,我认为没有最初的平等。 (人们熟悉的我-你形式的运用得到了辩护吗?)伦理上的不平等 (意味着):服从他人;原初的副职(意味着):“第一人称宾格”,而不是“主格”。因此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揭示的深刻真理常为人引用: “我们对每个事物和每个人都有罪,负罪于每一个人,而我比其他所有人尤甚。”当然,这种最高程度的罪并不是指任何个人的经历,也不是指做出这个声明的个人的性格品质。
四
这是一种不可转让的回应或责任,仿佛我的邻居在急切地呼唤我,呼唤的只是我,仿佛我是唯一的关涉者。亲缘本身存在于我的角色的排他性之中。把我对邻居的回应或责任转让给第三方,这在伦理上是不可能的。我的伦理回应是我的独特性、我的选择和我的“长子身份”。在布伯那里,宾格的我(the me)的身份和独特性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它们不是从对话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得出的;在对话里,这宾格之我是具体的。在布伯那里,它的“个体化”不仍隐含着实体论的东西吗?
五
处于相互性中的与他者的关系:在布伯那里,正义开始于我―你的内部。与此不同,从我的观点看来,从伦理的不平等(即我称之为“主体间的空间的不对称”)到“人们之间的平等”的过渡来自于国家中公民间的政治秩序。就我必须也要对“仅决于”我的邻居的第三方负责而言,国家从伦理秩序中的产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谁仅次于谁?我与邻居关系的直接性要受到一种必然性的修正。这就是要将人与人加以相互比较并对他们做出判断的必然性。于是求助于普遍的原则,即正义和客观性的所在地。但公民身份并没有终结我的中心地位。它授予这地位一个新的意义:一个不可取消的意义。国家可以根据存在的法则开始运转。正是对他者的责任或回应决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即它的正义性。
六
在布伯那里,对话有机地和原始地所归属的思想不仍是意识要素吗?对我来说,根本问题在于要强调:对他人的回应或责任不可还原为意识的意向性,不可还原为认知的思想,不可还原为与他者(theOther)的超越性绝缘的思想。这种思想,作为知识,保证了观念与被观念化者(ideatum)之间的平等,不管它处于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的(noetic-noenlatic)严格平行之中,还是体现为它的真理的充分状态,或者说是去“充实 (fulfilling)”意指目标的直观充盈(fullness),这充盈满足意指就如同一个人去满足他的需求一样。与另一个人的伦理关系、那种亲缘、对他者的回应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向性的调整;它是具体的形态:在这个形态中产生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同一个人对他者的关心和兴趣,即相同状态与那完全不相称于相同状态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与非“同类者”的关系。对他者的回应所保证的亲缘,不是因其区别而不能重合、不能融合为一的“单元(terms)” 之间临时凑合的联系,而是社会性所具有的新的和恰当的卓越之处。
这里,我讨论的方式,有些像从抽象意义演绎出“具体的情境”,而这些抽象意义的视域是被重构过的。这是一种被现象学所激发的方式,自从《整体与无限》之后,它便经常地被运用。例如,“在家(at home)”作为宾格之我(the Me)的屈折变化(inflection),要在住所的具体性中寻找,而住所的内在性则引回到女性的面孔。此外,它还强调“伦理内容”的具体性对于纯粹形式的(formal,形态的)结构所具有的必然性的限制:当“从属”是发布命令的无限者时,它就没有了奴态。在笛卡尔的上帝观念中,伟大者得较为渺小;可能性超出了父系中的可能的限制,等等。胡塞尔在空的形式和总是含有事物样的内容的一般(the general)之间做出了重要区分(《观念1》,第一章,第三节);难道这种区分中不包含着内容歪曲形式的可能(尽管作为一般化结果的种类从属于形式) 吗?
七
对于布伯来说,上帝是伟大的你或者永恒的你。人们之间的关系在上帝那里交叉,在上帝那里终止。我已经表明,相比于布伯,我不那么肯定:所谓神圣的人格 (Divine Person)就寓居在对话的你之中,虔诚和祈祷就是对话。我转而求助于第三人,或求助于我所谓的伊莱蒂(illeity,他性),转而谈及无限和神圣的超越,而它不是他者的他我性。这是上帝的伊莱蒂,上帝派我服侍我的邻居,为邻居负责。就上帝引起我自身和我的邻居之间的人际关系而言,他是有人格的。他通过他人的面孔向我显示,这种显示的意义不是被表达为显示者对被显示者的关系,而是被表达为向我显示的次序或命令(order)。在我的分析中,上帝在心灵中的出现总是与对他人的回应或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而所有的宗教情感具体地看都意味着一种对他者们的关系;对上帝之畏惧具体地看就是我对邻居的畏惧。尽管海德格尔强调情感的图式(schema),但这种畏惧的情感是不能回复到对自身之畏惧的。
八
布伯在基本词语我-你与我-它方面的二元论,一种社会关系和客体化的二元论,难道是不可克服的吗?我已经暗示了第三方与我的邻居发生关系的途径,以激发主位化、客体化和知识。难道社会性的为他者本身不是具体体现在给予上吗?难道它不是以物为先决条件吗?没有物,两手空空,对他者们的责任不过是天使之间的以太般虚飘的社会性罢了。
九
与趋向存在的知识形成鲜明的对照,布伯的语言非常忠实于与他者们关系的新颖性。难道这种语言完全打破了存在论的优先地位了吗?我-你关系难道不是以它自己的达到存在的方式被说出的吗?我曾试图通过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与那起到消除偏见(dis-inter-estment)作用的无限者的关系来进行思考。而“消除偏见”这个词在此有两种含义:它是关系的无缘无故,但也是在与上帝和他者们相关中的传统存在问题的遮蔽。在这种思考方式中,存在的意义问题成为关于存在意向(eonatus essendi)的质疑,在“对存在的理解”中,这存在意向一直是存在的本质特征:缘在(Dasein,此在)的存在意味着不得不存在。在对他人的回应或责任中,我的存在需要辩护:在那儿存在(being-there),不是已经占据了另一人的地方了吗?缘在之缘(The Da of Dasein)已经是一个伦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