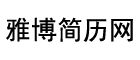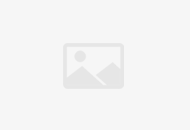刘醒龙的个人简介
刘醒龙,著名作家,1956年生,湖北黄冈人。曾任英山县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黄田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醒龙 - 人物简介
刘醒龙,男,祖籍湖北省团风县,1956年1月10日出生于古城黄州,1961年启蒙于英山县石镇区中心小学,1973年2月毕业英山县红山高中。
刘醒龙刘醒龙,著名作家,1956年生,湖北黄冈人。曾任英山县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黄田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了《圣天门口》、《威风凛凛》、《至爱无情》、《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等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分享艰难》等。《凤凰琴》被改编拍摄成电影。1973年毕业于英山县红山中学。历任英山县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及文化馆创作员、创作室主任,黄田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赤壁》季刊副主编,武汉市文联文学院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现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73年5月后成为英山县水利局施工员,1975年1月入英山县阀门厂,当过车工、车间副主任、厂办公室秘书、办公室主任等。1985年1月被调入英山县文化馆工作。1987年11月被调入英山县文艺创作室任副主任、主任。1989年4月调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任文学部主任、《赤壁》文学季刊常务副主编,黄冈地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1994年4月调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
2000年11月当选为武汉市文联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5月任《芳草》文学杂志总编辑。2006年11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刘醒龙 - 主要经历
刘醒龙是湖北黄冈人。高中毕业。历任英山县创作室主任,黄冈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圣天门口》等10部,小说集《刘醒龙文集》(6卷)、《凤凰琴》、《白菜萝卜》、《冒牌城市》、《挑担茶叶上北京》、《当代作家选集――刘醒龙》等近20种。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青年文学成就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其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背靠背脸对脸》获电影政府奖、金鸡奖、百花奖并入选百年华语电影百部经典,《爱到永远》改编的现代大型舞《山水谣》获文华奖。个人获庄重文文学奖,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1984年4月在安徽省《文学》月刊(即《安徽文学》)上发表处女作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1992年中篇小说《村支书》《凤凰琴》先后在《青年文学》第三期和第五期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在文学界有将这一年称为“刘醒龙年”的。2005年出版三卷本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该作品潜心六年写成后,先后获“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长篇小说大奖”和“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大奖决审团奖”。2005年6月、2005年11月和2007年1月,先后在武汉、北京及上海举行了《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
刘醒龙 - 人物作品
刘醒龙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弥天》《圣天门口》,出版有多卷本小说集《刘醒龙文集》及《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刘醒龙卷》《中国经典乡土小说六家丛书――大树还小》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四、五、六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七届庄重文文学奖和首届青年文学创作成就奖。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获国内外多种大奖。长篇小说《爱到永远》被改编成大型舞剧《山水谣》获文化部戏曲文华奖。高中毕业后当过水利施工人员、车工。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凤凰琴》等五种。出版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至爱无情》、《生命是劳动和仁慈》长篇小说《弥天》四部。部分作品曾多次获奖。获第八届重文文学奖,有些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刘醒龙 - 作品介绍
《圣天门口》――刘醒龙史诗性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到60年代,讲述大别山区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上,雪家和杭家两个家族以及他们周遭人物命运的故事。小说以大别山区天门口小镇为视点,展开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风云,题旨深邃,气象磅礴。
据作者刘醒龙介绍,创作《圣天门口》总共用了6年时间,其中开了3次头,废弃了17万字,写垮了3台电脑。这部长达三部、洋洋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刘醒龙在写作之初,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愿意,那就是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正名,同时也为自己正名。
《痛失》
作品以一个乡土小县的权力争夺、人、事流变为结构故事的纽带,以人性的变异为叙事元点,来建构乡村权力场,编织一个宏大的政治权力寓言。
作者凭勇气和正义感,写出了滋生腐败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这里的腐败分子不是道德有缺陷的人,也不是元能鼠辈。从任何意义上讲,他们都是精英。
作品直击乡村官场的龌龊、用人机制的缺陷,以及官要位主义的盛行。展示在你面前的是道德水准的“痛失”、“以民为本”的魂灵的“痛失”以及良知的泯灭与救赎的无助,充满深沉的,批判精神与悲剧意识。
刘醒龙 - 相关事件
《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部分发言纪要一部经得起读的长篇小说
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圣天门口》是一部大书,不仅因为它在风土人情风俗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描写堪称大气磅礴,而且里面有对历史的追问。认知历史是个艰难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如何整理成合乎逻辑的脉络,如何在历史中为我们自己定位,这才是历史。我们过去对历史有一套解释的概念,但历史之中有不解之谜,因此历史之中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圣天门口》就试图寻找说明其他的因素,比如性爱、人类之爱还有其他高贵品质。作家在叙述与情节之间的平衡做到了把握。
何西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就他的创作历程来看,《圣天门口》的确是对以往经验带综合性的一部大书,已经上到了当代小说创作一流的水平。刘醒龙早期的“大别山系列”的语言有些神秘特色,后来的《凤凰琴》开始改变了原来的风格,比较现实。但现在的《圣天门口》既能够看到早期《异香》中的神秘特色,又不需要猜谜。这几年长篇比较多,但经得起读的并不多。《圣天门口》是一部经得起读的长篇小说。
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醒龙花6年时间写的这部作品跳过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当代长篇小说艺术水准应该有而少有的高度。这部作品在艺术水准的提高之大是难以相信的,很出乎人的预料之外,这感觉就像当年读到《白鹿原》,有史诗性的气象。天门口可能是白鹿原之后又一个民族文化精神圣地。能做到这点就是作家最大的贡献。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圣天门口》是对作者与读者的双重挑战。刘醒龙有耐心,足以表达他的追求,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刘醒龙试图通过小说的复杂性表达打捞历史的奥秘。通常我们是从中国的史传传统和西方黑格尔所说的史诗传统来评价革命叙事和家族叙事文学。《圣天门口》既不是家族叙事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文学,它专注的是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是对已经清晰的历史的质疑。对历史的重新编码、对人类行为复杂性的叙述都是在以天门口为背景的历史叙述中完成的。
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的魅力杨至今(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中宣部文艺局对这个学术研讨会很重视,对这个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刘醒龙是我们热情关注、非常重视的一位作家,他的每部作品我们都关注和跟踪。他在创作中一贯关注时代、关注基层群众的情感和命运。他对底层人民的熟悉、理解和关心,让我们读者对当代和时代社会特别是农村有新的认识,他的创作对当代文学的深化发展有重要的启示。
梁红鹰(中宣部文艺局文学处处长):《圣天门口》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难得的收获。与作家过去的作品相比,《圣天门口》表现出由当下到民间、由现实到历史的一种转变,作家通过100万字的篇幅,描绘了中国近现代乡村变迁的历史。这部作品对文学创作的启示与价值在于:作家对历史的理解有独特的视角和追求,在文化探索上,对所写地域的地域文化以及方言的百科全书式的把握、对《黑暗传》的引用,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力量。
李敬泽(《人民文学》副主编):《圣天门口》这部鸿篇巨制让我们对作家的耐心感到惊叹。对此我有两方面的思考。十几二十年来的小说都很不习惯在小说中追求求证我们的所信――我们对生活、对历史、对我们自身的判断。这是长期以来我们不习惯的姿态。我们习惯的是告诉读者我们不信什么或者我们怀疑什么。作家面对的困难是论证他信什么。《圣天门口》对历史生活有很复杂的想法,打动我的是作家在百感交集的历史中雄辩地求证我信什么,即我们生活中高贵的具有普遍性的大爱以及使人之成为人的高贵的信念,这是很重要的启示。总的来说《圣天门口》很有创造性,对阅读与研究都有挑战。
陈美兰(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圣天门口》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怎么给它的价值定位是要认真思考的。是史诗吗?是现实主义吗?我认为这是一部悲剧性的历史寓言叙事。因此不在于人物是否丰满、是否把历史的方方面面都写到了,更重要的是要把历史寓言化。比如梅外婆和雪家女人的命运就是寓言化的一个案例。因此,我不同意有人说作家是站在基督教文化立场描写泛爱。另外,这部作品虽然是寓言化叙事,但作家并没有说教,而是用浓郁的生活、在世俗生活的碎片中思考历史,并且做得非常好。这是这部作品的经验与启示。
王强(中宣部文艺局影视处处长):对《圣天门口》我看重的是它对地域文化多角度全方位的展示。作家对大别山地区的建筑、风俗、传说故事、节日、民间工艺和生活方式等的挖掘与梳理既显示出作家对历史与生活的深厚积累,也流露出作家对历史与生活的饱满热情。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与竞争中,如何挖掘与梳理我们的地域文化,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的魅力,从而为建设先进文化做出贡献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圣天门口》通过天门口想象历史的走向,它使我们想到李氯说摹洞蟛ā泛汀端浪⒗健贰@吠兴豢伤家橹Α!妒ヌ烀趴凇吠且教侄20世纪历史的认识。从家庭到国家、从家族到民族、从敌人到朋友,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的发展也是现代国家兴起和建立的过程。《圣天门口》用超越性的眼光、通过历史生活的生动描写完成了这个过程,在天门口的绝望之处正是新的时代、新的民族诞生之处。天门口预示了历史的新的开始,这就是和平建设和和平崛起的一个新的时代。
开创了历史书写的第三个阶段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2004年以来中国的长篇小说有些奇特的地方,比如写《狼图腾》《藏獒》,现在又出了写一个村庄的《圣天门口》,但它写的是一条“龙”。《圣天门口》有几个特点,一是这部作品的小说性很强烈,避开当下写历史需要沉淀,不然就写成了问题小说。刘醒龙是有充分的艺术积淀和生活积淀的,他能够在历史之中从容地把握历史,通过一个小村庄写了大历史。二是小说的构思和行文是非常严密的,看不出明显的历史阶段,历史不是夸大地无限进入,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描写、通过细节悄然进入文本、进入人物的命运、进入小村庄的变迁的。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圣天门口》是一部有多种蕴涵的作品。90年代以来,文学一直在寻找精神力量。在怀疑、拒绝、颠覆之外,一批作品转向了宗教。《圣天门口》让我想起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写出了新的东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一条线索出现得晚了些,但丰富了这部作品,增加了新的思想线索。
汪政(江苏省文联):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多卷本作品的。我认为《圣天门口》开创了历史书写的第三个阶段,与传统的历史叙事相比,新历史主义是第二个阶段。但新历史主义没有对认识历史提供新的东西。新历史主义只是对历史进行消解,在对历史重新编码后新历史主义并没有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花腔》是这方面的代表。刘醒龙是有勇气的,他不是停留在编码上,而是通过繁复的人物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中的家族、个人到历史动机、历史理想与选择等回答了历史是什么。这就是超越。
胡平(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关于历史有一种写法,就是你都能读明白,但不知道作者要写什么。这种写法很安全,但读者不会满意。但如果要对所写的加以判断就要冒风险,这需要勇气。刘醒龙是有勇气的,这样写作让人肯定和敬畏。他有自己的信念和判断,他从不回避历史与现实所面临的问题,能够直面社会与人生。刘醒龙通过几个家族的男人女人在历史变化中的恩怨情仇把历史的、生活的、政治的等等都表现出来,概括反映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且由于他把握得比较稳,所以作品达到了一定的永恒。
牛玉秋(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写长篇小说是要气力的,之所以有半部长篇的说法,正是因为有的长篇气力不够,《圣天门口》读到最后一页给人的感觉是气力贯底的。作家不仅有气力、耐力,同样也有胆识和智慧。我认为这部作品是三部分的有机结合,即历史、寓言和说书。把这三种东西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挑战,如何实现作家的梦想是一个精神建设问题,它不仅是作家刘醒龙一个人的责任,是整个文化界的重任。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对长篇小说惯常的认识是“市民社会的史诗”,20世纪最好的小说都是家族小说,那么醒龙写的是什么?我认为《圣天门口》写的是乡绅文化,不是农耕文化。市民社会在中国没有形成,在西方也已经碎片化,因此,中国家族颓败是因为乡绅文化不能应对外来文化,当它不能应对时,天门口的那些悲剧就会发生。《圣天门口》为认识和理解中国家族颓败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圣天门口》是对作家实力的考验,即对作家对方言、民俗、风情的把握的考验。没有这种把握能力是不可想象的。应该说刘醒龙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从作品中看不出来作家是站在梅外婆的立场上或者说基督教文化的立场上来进入历史叙述,对历史的把握是很难的,用历史理性把握都不容易,更不用说用其他的方式。因此,作家事实上写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本体或者说是呈现心灵。我不赞成把历史加在作家或作品身上,要一个作家对百年中国历史做出条分缕析是很困难的,也是过分的,当然我们不能回避历史。
洪治纲(浙江省作家协会):我也不赞成把《圣天门口》与基督文化联系在一起。《圣天门口》所强调的扶弱济困、友爱互助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伦理传统,我也感觉不出作者是要用基督文化解决暴力问题。作者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暴力之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构建和谐社会。这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很大的跨越。
对史诗品格的追求吴义勤(山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圣天门口》是一部能够满足我们对于长篇小说这个巨型文体的传统期待而又在艺术上有耳目一新之感的作品。作家在思想艺术领域进行的大胆探索,既表征了当下长篇小说写作的某种高度,又似乎代表了长篇小说的又一次重新苏醒,代表了当代中国作家重回长篇小说“正途”并再现长篇小说文体魅力的一种自觉努力。《圣天门口》对史诗品格的追求可以说毫不隐讳。作家的艺术理想是建立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并对之进行阐释。《圣天门口》还是一部在艺术格调上极其大气的长篇小说。思想的大胆,艺术的敏锐,才气的奇诡,以及生活和文化底蕴的厚实,都使小说呈现出难得的大作品才有的魅力。
施战军(山东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圣天门口》的贡献是对中国式叙事的贡献。这部煞费苦心的作品试图通过对历史的综合、反思和重建某种信念,表现了中国精神支柱建构的过程及艰难。
吴秉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圣天门口》里面有许多超越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如善良、仁慈、友爱等不能理解为是宗教文化,这是人类美好的品质,是人类的理想。准确地说这是一种道德情感和道德情怀。
王春林(山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我看来,《圣天门口》如同《秦腔》《平原》一样,不仅是2005年度具有年度标高意味的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也可视为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与“革命历史小说”相比较,《圣天门口》值得肯定的是它摆脱了一种狭隘的叙事立场,与“新历史小说”相比较,《圣天门口》没有走向历史虚无主义,而是积极地进行着一种艰难的建设工作,作家通过自己对于历史的个性化叙述过程而最终确立了一种终极的精神价值立场。因此,《圣天门口》实际上是一部含纳、融会了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艺术优势,然而同时又突出体现着刘醒龙巨大创造性的集大成之作。
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一般而言,刘醒龙所面对的是书写对象,是现代中国相当厚重而浩漫的历史,极容易处理为“宏大”而“壮阔”的历史“史诗”的社会革命编年史。但是《圣天门口》的视角却死死盯在天门口这个掩隐于大别山区一个乡间小镇。相对于宏阔而浩荡的中国政治、革命、战争、经济、文化的历史风云而言,它只是一个特写,一个碎片,然而,正是立足于天门口这方寸间的弹丸之地,刘醒龙却展现这厚重历史的精气神。
刘醒龙 - 人物影响
刘醒龙的小说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海外也很有影响,美国的一位女作家翻译了他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把他看作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前几年还特意来中国,并到刘醒龙的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湖北英山,实地考察大别山一带的风土人情。为此醒龙还特意邀请了我一起参加,见到了刘醒龙的父母及家人。可能是因为刘醒龙的父亲也是县里的乡镇干部,他家的小院挺漂亮。种着的石榴树高高地悬挂着果实,还有伺弄的十分整齐的花草。醒龙在老家当过工人。英年早逝的作家姜天民在县文化馆工作时,是他的兄长和朋友。姜天民因小说获全国奖而被调走后,醒龙就被调到文化馆搞创作,就连所住的宿舍,也是姜天民先前住过的。以后,他也被上调到了黄冈和武汉。大别山一带的风土人情在我看来到也没有多少人杰地灵的环境,相反和其他山区一样,凭借那样的人文气息,刘醒龙的平步青云显然要有着超常的毅力和信心。的确刘醒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做任何事,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打扑克、打麻将,总有那么一股不服气和不服输的劲头,甚至是不求输赢,只要一时的酣畅。他新出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一百万字,囊括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文化的厚度和复杂人性的深度,前后花费了六年时间。在我看来其动力也是出于那么一股不服气和不服输的劲头,因为当时在《弥天》的研讨会上,有评论家发言认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到《白鹿原》已是不可超越的,谁再写也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想刘醒龙的那口气一直憋着,直到《圣天门口》写完才放松了。
凡见过刘醒龙“风华正茂”的模样,很难料到刘醒龙也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尤其是他讲话的语速快捷有力更显得精神抖擞。惟独他的语速放得舒缓甜美之时,那一定是在和家里的小女儿说话。
湖北作家刘醒龙似乎无论春夏秋冬一直留着短短的小平头,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初次见面是上海文学召开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研讨会上。那时他的小说《分享艰难》几乎成了整个研讨会的关键词。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尽管他也坦言“分享艰难”不是他的原小说名字,而是周介人给他改的,功劳还是应该记在周介人身上。但是刘醒龙这个作家就此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之列。一位前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要求全级干部,都要看根据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改编的的《凤凰琴》,并并更是要求一定要要解决好乡村民办教师问题。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也的确请他来写过主旋律剧本,然而似乎又没有搞成,不知怎么回事?那几年,他一下子完成了四五个长篇小说,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还给他的《弥天》也开了研讨会。因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当然谈话的内容主要还是小说创作,从他的话语里偶然会流露出自己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上有所顾忌。他似乎更愿意人家说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
刘醒龙 - 人物评价
刘醒龙是朴素的,为人朴素、为文朴素。在一个流光溢色、追逐时尚的时代里,能保持一份朴素的心性是多么的让人佩服。朴素的刘醒龙不管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有多少闪亮的头衔,总是执着、谦逊地行走于他的艺术世界中,在黑色的土地上,把心交给那些承受苦难、抗拒苦难的人们,总是能够避开流淌于生活表面的泡沫,看取生活的真相,把民间底层人们的精神和灵魂真实地表现出来,以坚硬的抗争和如水的柔情给人以深深地感动。
“过去”的刘醒龙和“现在”的刘醒龙,在我的感觉中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变化,想象中,他心灵的上空总是有鞭子闪击而出,抽打着他的良心,拷打着、逼问着他是否忘记了与他一起成长的父老乡亲们,是否忘记了土地上的人性最本质的内核是什么,于是刘醒龙不敢懈怠,不敢有所取予和忘记,他象“追日”的夸父,越山趟水,在漫漫乡野寻找着灵魂的真谛,在《凤凰琴》山村一隅的角落看到了贫穷教师的高尚精神,在《大树还小》的山坳里,发现了人性的美丽与痛苦……,当他一旦意识到自己离乡土太久太久、太远太远的时候,内心里就有了隐隐的不安,他在《弥天》这部长篇小说的序言中谈到内心的这种感想时,特别让我感动,他说:“不知不觉中,对过去的痕迹产生莫大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在我心情郁闷时,这痕迹就像乡土中飘来的炊烟,时而蛰伏在屋后黝黑的山坳里,时而恍恍惚惚地飘向落寞的夜空。假如我的心情不错,本是无影无踪的痕迹,就会是雨过天晴之际,经由那肥硕的蚯蚓一耸一耸地爬过,犁出一条宛如房东女人的粗针大线,并且象小路弯弯的五彩和七色。更多的时候,心平如水,一切如同从来没有发生。痕迹便成了秋收之后弥漫在田间地头的各种野花,有四瓣、有五瓣,有墩实,有轻盈,那是狐狸和黄鼠狼,还有狗獾、猪獾,甚至还有果子狸,总之都是小兽们留下来的脚印。”乡土世界的细微之处能在一个人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痕,他的情感就会有一种沉重的悲凉和柔情的深刻,过去的历史、生活过的乡村与他就有了一种血肉相连的生命关系,怀想过去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抚慰,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和生命旅程中,看到“过去”在为“今天”提供哪些有益的东西。
由这朴素的乡土之情,可以理解刘醒龙在日常生活中对朋友的纯朴之情,理解了他从不伤害别人的那种谦逊的生活态度,更理解了在《弥天》这部长篇小说中,他对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扭曲所表示的深深的愤怒,对留给这块土地的惨重创伤的刻骨回忆,在灾难和不幸面前,他美丽的怀想,没有了缠绵和柔情,柔情退隐到了文本的后面,生发出的是批判的、尖锐的声音,他用利剑挑开土地上上演的荒诞,看到人性变异的原因,看到人的疯狂和丑陋,但他从未对“人”的心灵之美失去注目的信心,在《弥天》中他写到一个细节:作品的主人公温三和病重时,按照乡村的习惯去“叫黑”,作为“封建迷信”活动,在当时是被严厉禁止的,然而领导人乔俊一却偷偷地和温三和的母亲达成默契,去完成这样一种乡村的“仪式”。作品中这一细节在我的感受中有别样的魅力,它是民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信任、同情的一种伟大精神,它让人在残酷中看到了诗性、在疯狂的人性裸露中感受到了人之“为”人的温暖。这种“深刻”大概只有象刘醒龙这样把“心”安放于土地中的作家才能有,这是刘醒龙作品的底色,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