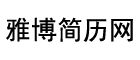南往耶的个人简介
南往耶(Nailwangxvib),短裙苗族,蚩尤后裔。诗人,记者,批评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于黔东南雷山县的独南苗寨,出身农民,但狂傲不羁。被人多次陷害。曾供职于《贵州民族报》社,担任记者、编辑;现在文化部《文化月刊》杂志社工作。他在《贵州民族报》策划并主持的文化专栏“南往耶对话中国100位作家诗人学者”系列访谈,及主编的《雷公山诗刊》,引起文化界关注,人称“铁腕记者”、“诗坛少帅”。他是中国第一位用汉语写作的短裙苗族诗人。创作有《南往耶的刀锋》系列长篇杂文随笔等。其祖父系国民党雷山片区高级将领。人物档案
南往耶(Nail wangx vib)男,短裙苗族。诗人,记者,批评家。八十年代出生于黔东南一个叫独南村的苗寨,农民家庭出身;母语是短裙苗话。曾供职于《贵州民族报》社,担任文化版记者、编辑。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国家级文化类核心期刊《文化月刊》杂志社工作,担任记者、编辑。其策划并主持的“南往耶对话中国100位作家诗人学者”系列访谈,以及业余编辑的大型民间诗歌刊物《雷公山诗刊》,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文化界的强烈关注。他是中国第一个与国内外众多高端文化人物对话的少数民族记者,也是中国第一位用汉语写作的短裙苗族诗人。热爱绘画和写作。有小说、随笔、评论、访谈散见各类报刊。创作有《南往耶的刀锋》系列长篇杂文随笔等。
2011年底至2012年初,由于南往耶在其博客撰文批评贵州省作家协会领导的文学作品和片面揭露他们中某些人利用手头权利谋赚情色勾当,及极力肯定作协外作家而不是作协里的人,笔触老辣,刀锋犀利,因此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于2012年1月29日向贵州省省委宣传部提交文件“举报”南往耶,贵州省副省长谌贻琴接手审阅签署。罪名上声称南往耶已经“被境外势力所利用”,属于“反华势力”,使之从普普通通的文化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成为贵州作家协会自1953年成立以来首次公开打压本土青年作家的事件,也是贵州方面继文化大革命时期贵州诗群所受迫害以来最黑暗的文化事件。而一直追求真理的南往耶,不畏强权,事件之后于2012年5月13日发博《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南往耶正面挑战贵州作协主席团》一文公然曝光贵州作家协会的这一丑态,使全国上下为之震惊,一片哗然。至此,一系列深度的文化访谈塑造了一代个性鲜明的少数民族记者形象,加之铁骨铮铮,有“铁腕记者”之范。
人物近照
南往耶照片
人物言论
诗人论如果你不是写诗歌的这块料,南往耶一眼可以看出,我奉劝你立即改行。现在有些人说到诗歌的时候,好像总是说诗歌是文学所有文体中的最高的艺术,是最能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文体。每每听到这些,南往耶想说的是,这些人在不承认其它文体价值的时候来写诗歌是要不得的,是不配写诗歌的。而若是说诗歌才是最能直抒胸臆的话,我想散文随笔这种文体更能更好地道出心里话。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不应该挤到诗歌这里来送死或者装才华,以及在这里捣乱。才华不是诗人的专利。为此我顺便唠叨几句,真正的诗人是有疼痛爱好和悲悯情结的怪物,是历经万难而不倒的枭雄,而不是那种实际上也的确著作等身的诗歌机器人。在中国,能称得上诗人的当推司马迁、曹操、鲁迅和李敖,以及毛泽东、蒋介石和朱F基,因为这些人用复仇式的大恨大悲去爱,用孤独和痛苦去思考。而屈原、海子、顾城之流者,我认为不完全是诗人,抵多只是生活现实中物欲的叛逆者,因为他们过早地选择了死亡。死亡在大诗人真诗人这里是一种逃避,一种对生命对历史现实的不负责任。这不是说诗人不可以死,而是他们的死未免太过浪漫了一些。今天我们对这些有自杀天赋的文人墨客的怀念,应该是一种对文化天才的怀念,而不应该是对诗人的怀念。认清楚了这一点,中国诗歌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有救了。
书生论读书而只能悟道明理,作文而只能修身养性,这于雄才厚积的奇人实在是天大的浪费和侮辱,是对万类众生的不负责任,是苟且偷生,加之中国的文学界正进入了清朝后期,因此南往耶必须出山。但话又说回来,这里有一个条件,倘使一个人生来而在世上却没有历经什么大苦大难,不具备大恨大悲,那么这个人就算有万千的知识也不过是绚丽多彩的才华而已,而不是奇崛险峻的智慧,这样他就不可能创造传奇。这经历南往耶又到底有没有呢?这个我就没有时间也没有纸张更没有兴趣告诉大家了。行家一出手,你就知道有没有。天造万物,我创唯一,对《雷公山诗刊》能否孤绝奇骏我充满了信心。差不多了,还是回到诗歌或者诗人这里来吧,送诸位群雄一句话:我认为,诗人应当必须清高狂傲的。但是若你腹里没有诗书,那么你的清高就是无知;如果你的胸中到处山水,这样你的狂傲才是境界。我的意思是,诗人作家应该首先是英雄好汉,然后才是文人墨客。有不知道这个的,大家应该向南往耶学习。
诗歌论诗歌这种高贵的物种本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为了传授并阐述我的观点,故而长篇大论了这些废话。竟然说到了这些,那也应该说说诗歌和诗人这么个行当。有的人生来就只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搞诗歌的诗人们都是为了“诗人”这个头衔而来的,写些无聊的诗句,然后拥有诗人的身份,以便于骗取文学女青年。在他们眼里,诗歌就是春药,就是袭击女人阴蒂的跳蛋。仅就春药跳蛋论,这原本没有什么坏,还很风趣地承认了诗歌的价值,但它的不好就在于他们原本是在藐视诗人和诗歌的。世道啊,写一两首诗歌就能够让女人脱裤子的话,何乐而不为呢?而事实上却有女人也写诗歌的,这不会是她们在搔首弄姿袒胸露乳地挑逗同志们吧?岂有此理。
民刊论这年头大家吃饱了没事做就流行起做民间刊物来,而诗歌这一类东东的又得天独厚,所谓诗歌嘛就是把一句很像话的话说得不像话便就是了,这给有“主编病”却只有小学生水平的众兄弟们有了绝佳的机会,诗刊因此雨后春笋起来,并像被侮辱了多次的三陪小姐一样厚着脸皮光明正大地招摇过市。虽然这些三陪民间诗刊算不上有艾滋病,但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季节里,多少还是有点阴部瘙痒的。南往耶是不喜欢有了性病的感情交易的。我的意思是,现在太多的这种有性病的民间诗刊甚至官方诗刊成全了越来越多的伪诗歌伪诗人,并成大势,真正的诗歌和诗人被它们给混淆了搅乱了,毫无容身之所和立说之地,因而被那些没有眼睛只有屁眼的世人错看至于唾弃了,实在可悲。因此南往耶不得不挺身而出,亲自操刀,刀锋直指中国诗歌。
贵州论我是黔驴技穷的“黔”这里的人。在此先不说驴技是否真的穷了,先说物质上的穷吧。必须承认,贵州是一块贫穷落后的地方。而贵州为什么贫穷呢?有人帮我们回答了问题,说是山高水远交通不方便,这样就不利于走出去和走进来而致使的。这的确是个问题。果然,西部大开发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还挺热闹。近年来,贵州的山村相继通上了公路,有的山村还通了县道的,被大路穿村而过。在黔东南,这无疑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居山野的苗族侗族儿女终于看见公路修到家门口了,终于看见车子了,终于有了城里人的感觉了,终于可以呵呵哈哈嘻嘻了,终于了了了,实在是很终于的。只是没有人去想,修通了公路该怎么用。我本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其它的地方我不知道,就只说我家乡黔东南吧。国家拨下来的巨款把很多山村里的泥土小径铺成了水泥路,把原本土木结构的茅房变成了砖头和地板砖砌成的新型厕所,把老朽的吊脚木楼换成新的,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稍微还有点意思的是,偏僻的山村里终于有了钢筋水泥筑就的有四五层楼高的砖房学校了,这多好啊。但请恕我直言吧,这些不过是地方政府为了应付国家指标而所为的,因为在所有的西部大开发中,在所有的基金会中,在所有的旧颜换新貌中,竟没有在任何一座山村建立一个图书室。我南往耶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给久居山野的他们足够的理解、消化和承载外来城市文化的准备,那么,所有向他们送上去的文明和进步都是堕落的副产品,是对他们最大的伤害,是谋杀和摧残,是犯了天罪的。因为这种强制性送去的便捷、快感和幸福,所导致的结果是,让富人快速地富起来,让穷人拼命地穷下去,而文化缺失的他们最终忘本,带着理直气壮的贵族姿态狗娘养地活下去。在这里,公路最大的功能不外乎是让外来文化更好地走进来和不能让他们有文化地走出去。我们应该知道,外来城市文明的直接潜入,让他们无法消受而变得世俗和浮躁,同时也有便于那些文化盗贼的顺手牵羊和叛变与出卖,这又让他们惶恐不安而提防起邻居甚至亲人。当乡村变得如此现实如此城市的时候,他们所浮现出来的富裕其实是表面的,他们骨子里依然还是贫穷甚至堕落。因此我想,应该让贵州大山里的子民先拥有文化,拥有了文化之后他们才能驾驭财富拥抱文明。
人物评传
合影?见证南往耶对话中国100位作家诗人学者系列照片
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霍俊明评论尽管南往耶在写作年龄和被诗歌界认可的程度上肯定是一个“年轻”诗人,他的诗歌写作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不足,但是他的诗歌写作向度显然在当下的时代具有某种重要性。他的诗歌有意识或不自觉地呈现出诗歌和生命在文化地理上的对话、摩擦甚至碰撞。由此,诗歌的地理性、差异性以及个性由此产生。而我们已经目睹了个体、自由和写作的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作为个人的写作可能会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仍会延续下去,因为这个推土机和拆迁队无比疯狂的年代同样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话语”。这种诗歌写作的寓言性和“政治话语”是必备的,但是其前提仍然是个人化和诗歌本体意识的,我们不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诗歌话语权力的争夺者以及在主流美学的规训下“思想”和“写作”一起被征用的流行的“底层诗人”和“现实主义诗人”吗?尽管南往耶也属于底层中的“打工”者,他的一部分诗也呈现出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痛苦,但是这些诗歌不是目前流行的“打工诗歌”。因为南往耶能够基于个人经验和想象力在体现出介入现实能力的同时,更为可贵的是他立足于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故乡“雷公山”的展现的既具有个人性又具有时代性的文化乡愁和精神传记。但也想提醒南往耶的是,目前看来“底层写作”、“打工诗歌”、“新农村写作”已经成为一种被“官方”和“民间”双重鼓动的大量复制的流行性写作。而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者的诗歌写作在此语境下其挑战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我知道对于南往耶而言他的生存的语境很大程度上就是最为真实也可能最为残酷的“打工”生活。而南往耶对“出生地”“独南村”和“雷公山”的个人记忆和文化乡愁显然体现为诗歌写作中就具有了重要性。在此意义上,南往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着“低烧”的诗人。他以骨刺一般坚硬、疼痛的方式刺向一个时代病困重重的子宫和躯干。
甘肃西北民族大学青年作家范宇评论他高傲的头颅不需要恳求任何人的理解,而懂他的任何人都将毫无保留地理解他。
南往耶的狂傲,或许有点夸张,但绝没有半点虚伪。雷公山下的南往耶是苗家的儿女,他的铮铮傲骨便不难理解。据说苗族是蚩尤的后代,这一点苗家儿女们一点都不避讳,反而大大方方地承认。传说蚩尤有八只脚,三头六臂,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善于使用刀、斧、戈作战,不死不休,勇猛无比。作为蚩尤后代的南往耶,或许正是流淌着蚩尤的血液,蚩尤的无所畏惧,南往耶毫无半点排斥地继承下来。蚩尤最后败给了黄帝,战败的他虽饱受种种非议,但似箭如梭的岁月终究抹不掉他的铁血傲骨。而今天,谁能够战胜蚩尤的后代南往耶呢?我想没有,如果有,那也一定是一种叫做诗歌的东西,南往耶只愿意死在诗歌的剑下,无怨无悔。
写这篇文字,正是深夜,清冷的西北有些苍凉的月光。窗外的荒山,有了这些月光的装饰,满怀信心,挺直了它们的腰杆。西北的月光,让人想到的不是江南水乡的温婉,而正是像南往耶一样的豪迈或是狂傲。兰州离盛唐的长安不远,打个盹就到了,这不,月光下一位行吟诗酒醉半酣,像是吟诵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盛唐,这是绚丽的盛唐,那个醉酒的诗人,莫非就是万世景仰的李白。
是的,他就是李白,高歌“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力士脱靴,贵妃磨墨,他的狂傲不羁,挤不进政治的夹缝。挤不进正好,山山水水,放浪形骸,与朝廷无关,只做一个酒醉的诗人。“我是天才我怕谁”,盛唐容不下他,他却驾驭了一个盛唐。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一诗中有这么一小节: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写得正好,盛唐之外的李白完全有这个气场驾驭半个盛唐。
而今天的南往耶,真是像极了盛唐的李白,一样有着“我是天才我怕谁”的凌厉傲气,一样有着“仰天长啸出门去”的飘渺洒脱,一样有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桀骜不驯。或许,南往耶的狂傲终究被逼的四处逃窜,但他一定不会低下他的头颅,他的头颅只为诗歌而生。我想,今天的世俗如若容不下南往耶,或许千百年后,南往耶会像李白一样驾驭半个今天。没有半点夸张,蚩尤的后代,怎会那么轻易低下他的头颅?
南往耶,不居庙堂,只持一把长剑行走江湖。相信他的剑气,像李白,挥袖一舞,便是半个中国。
因为,南往耶手中的剑,有一个超凡脱俗的名字,叫:《雷公山诗刊》。
中国当代著名女诗人安琪评论贵州这地方要么不出人,要么就出奇人怪人,譬如黄翔,譬如哑默,譬如梦亦非,譬如南鸥,譬如新近锋芒毕露的南往耶。你只需稍稍翻阅一下南往耶博客和他担任编辑的《贵州民族报》及担任主编的《雷公山诗刊》,他毫不遮掩的个性扑面而来。
我天生对张狂的人有同类相惜的亲切感,这符合“吾道不孤”的老话。一个人但凡有才华了总像针尖难免要刺出布袋,又像烈火总要烧出包裹它的外物,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更没有办法的是,针尖一刺出总难免要刺到人,烈火一烧大也总难免要烧到人,即便不刺人不烧人人也要躲之乃至拗断之浇灭之。这就是才华张狂者的宿命。对南往耶,我一直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他既要保持才华又要收敛个性,这当然是中年之人的中庸之语,也是失败于生活现场的垂暮之将对正在沙场征战的少年英雄的关切之情。但我深知,那正驰骋于诗歌疆域的人他坚定的目标只会注视诗歌的一切,他无暇也无心于琐碎的杂事俗事。这就是当下的南往耶状态。
这样一个热血与激情共舞的诗人来做事,容易出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份专属民族体系的报纸被他创意十足的想像力和行动力编辑成了一份大文化、大视野、大胸怀、大关怀的动人篇章。我们也看到了雷公山这一座独属于贵州的山走进了全国诗人的眼中心中。每个人都是地域的人,他的一举一动事实上都暗中肩负着传播地域的作用,只是有的人自觉有的人不自觉,南往耶无疑是自觉的。
这样一个胆识与勇气兼具的诗人来做事,也容易出状况,对此我只有再次提醒:珍惜生命,永远诗歌。
河南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马新朝评论我想他一定是个诗人,不然他的声音不会这样丰富,像是蕴含着某种矿藏,不然,它的声音不会暗藏着洞穿空间的锋芒。他就是南往耶,贵州诗人,他办一份民办刊物叫《雷公山诗刊》,我把雷公山与南往耶联系在一起,它们虽然是一山一人,但我总是疑怀他们中有着某种联结。是精神的,还是气质的,还是文化的,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雷公山地处苗族腹地,在黔东南境内,那里景美人美。这份《雷公山诗刊》不仅有着雷公山的骨络,也会有着苗族儿女的气血。想到这里我被自己感动了。我感动的是一个青年诗人,找人资助办一份民刊,这中间的艰难和对诗歌的热爱。中国诗歌仍然是中国文学最为活跃的部分,而民刊和网络又是诗歌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民刊和网络中的诗歌起到了中国诗歌的引领作用,相对来说官办报刊的诗歌却当滞后。然而民刊和网络的诗歌成果却在影响着官办报刊的诗歌。这已经是不争的实事。近30年来,中国诗歌由对公众经验的写作转向对个体的尊重与人的内心的写作,这种巨大的转变来得无声无息,这主要是民刊和网络的作用。在南往耶的博客,从南往耶的一言一行,我感知到《雷公山诗刊》是贵州最值得期待的一本刊物,也是中国最值得期待的一本刊物,因为它出身民间,且真正代表了民间的声音和性格。一份民刊的性格就是它的主编的性格,而南往耶是狂妄的,因此,我们看到《雷公山诗刊》不甘平庸,锋芒处处,好诗连连。而锋芒正是民刊的存在的理由。
20世纪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说了一句世人震撼的话:“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雷公山诗刊》,我隐隐地从中听到了雷公山的粗重的嗓音,还有一千多万苗族人的心跳以及篝火旁的说话声。一份诗刊为一座山说话,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说话,它的声音我听到了,很多人都听到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黄恩鹏评论去年南往耶办《雷公山诗刊》,我就觉得这小伙子有股冲力。这冲力是针对疲软的中国诗坛的。他眼力厉害,管他教授还是学者知名大作家大诗人,作品不好坚决不要!当期他发起了“钓鱼岛诗歌”征稿,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振奋民族精神的好举措。可惜中国诗坛群体阳萎集体虚脱,哪一家刊物也不敢作这样的征稿。南往耶做到了,做的非常成功、给力。我称之为“民间军旅诗”一点也不过!
好山好水出好诗人,南往耶是苗族的儿女,他年轻有朝气,他的“狂”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他的才气和写作的冲劲让他有本事狂。雷公山清纯的泉水滋育他的心灵,洗亮他的眼睛。他直接、坦诚、不转弯抹角,不掩掩遮遮,写诗撰文时不时迸出一句糙话。我欣赏这样的性格。这种性格能成大事。如果他是一位军人就好了,他一定能振兴中国军旅诗,免得一些人整天自恋似的把糠心儿蔫萝卜当手榴弹扔来扔去制造着轰炸效果。当然,南往耶的狂,也不是独自在那里狂欢,更不是巴赫金式的集体心灵的狂欢。而是一种人性的真正释放。我欣赏他的出口无忌。因为无忌的人生才会产生不羁的力量,才会有独立的思想和顿悟。从而让语言构筑的思想光芒冲破束缚,照彻广袤的心灵大地,从而让文学得以进步。在这种有意无意的“狂放”中,一颗心不再害怕权威,也不再前后设防担心什么。我就是我,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某刊物就是垃圾刊物,某文字就是一堆垃圾文字。敢说话,敢置疑,敢批评,敢担当。多好。看这无忌的力量,让一本正经见鬼去吧。文化的反智慧主义让独立的思想找到了一种可以喷射的出口。
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诗人南鸥评论南往耶是一位年轻的画家,从他的话语间我知道创办《雷公山诗刊》是其深思熟虑后的一个重大决定,而这个决定对他的生命形式是一种考量和挑战。我时常在想,多元和飞速颤变的今天,人们对生命形式的选择远比我们那个时代辽阔而丰富。面对日益世俗的图景,他为什么依然选择日渐凋落的文学呢,为什么对文字依然保持如此的虔诚和敬畏呢?他的普通话与我一样的生涩,就如同贵州高原蛮荒的质地。坐在他的对面,一种大山一样朴素而刚毅的品格扑面而来。尽管他披肩的长发和俊亮的眼睛所显现的几许飘忽也许会被人误读,但我就像坚信大山的质朴和坚韧的品格一样相信他的话语。无疑,这位年轻的画家让我感受到了一股从海底汹涌而来的意志和力量。也许,他此刻的想法只是青春年少的激荡,还没有形成一种坚定的信念,但我想暗夜里的一束微弱的烛光,她给人的温暖与力量一定远远超越她自身,远远超越那些光芒四射的风景。她已向我们昭示一种存在,演绎出一种存在和诗性的力量,也许,我们由此会听到万物颤动的声音。
尽管,他的话语流露出些许的狂妄,但我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狂妄,因为他所有的奢想都是出于对诗歌的虔诚和敬畏;因为我更喜欢激荡着霍尔蒙气息的骚动不安的灵魂;因为我不能再把那些四平八稳的近乎于完美的平庸视为才华,而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宽容、理解和支持。
雷公山是贵州黔东南腹地海拔的标高,它的奇峻、孤绝孕育的古朴、灿烂的苗族文化越来越被视为世界文化的瑰宝和人类灵魂最后的栖息地。我想《雷公山诗刊》的版图应该是整个现代汉语,而它海拔的标高应该是当下诗歌奇峻的海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