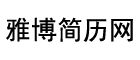潘光旦的个人简介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男,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后以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笔名光旦(见1929《新月》),西名Quentin pan。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除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外,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
个人履历
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
1922年,毕业赴美留学,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对于谱谍学深感兴趣。
1926年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然成了右派罪行之一, 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常看见这二个人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费先生)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文革时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已经成为危重的病人,却得不到任何治疗,为了尊严,他坚持回到自己的家里。
1966年,潘光旦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着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拒绝。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生一样爬行着除草。
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
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 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
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学术成就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那代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行结合的最早成功的范例。
主要著作
《冯小青》
《中国家庭之问题》
《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
《读书问题》
《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
《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近代苏州的人才》
《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
《家谱学》
《优生概论》
《人文史观》
《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
《优生与挑战》
《自由之路》
《政学罪言》
《优生原理》
《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
《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
《湘西北的中国“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教育思想
重读潘光旦重读潘光旦在1949年以前那些谈教育的著述,重温他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教育思想,重现潘光旦教育理论的现代意义,重新解读潘光旦在教育上恪守并践行的那些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近代中国会出现教育技术化的不良倾向
潘光旦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每一个人为目的,必须在每一个人身上着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个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为了促进个性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专家人才必须完成人的教育后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的意义上的专才,否则只能是优良的工具。
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潘光旦并没有停留在对中国近代教育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的梳理与概括上,他在有关著述中进一步回答了关心教育的人们在读了他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概括后可能提出的疑问:为什么近代中国教育会背离对人的全面培养这一根本原则?为什么会出现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的不良倾向?
潘光旦发现应该以人为研究本体的社会科学并没有拿人做对象,社会俨然成为一新的本体,于是社会科学成了从社会到社会的本本,成了隔靴搔痒不着痛处的空谈。而作为社会科学一种的教育,其下手与对象也就不能无误了。于是教育成了“社会教育”,“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教育必须配合社会需要”――这些说法乍听起来颇有些冠冕堂皇,然而潘光旦指出,正是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及做法,才使教育误入专业化、技术化歧途。专制主义政体的国家里,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是很普遍的现象。不过,也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社会里,虽然没有了极权统治,却也会出现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现象,这是长时期的极权统治留下的幽灵仍然左右着人们的观念行为的缘故,是缺少思想的人们只会从眼前利益着眼行事的结果。市场需要专业技术人才,急功近利的人们又迫不及待地希望受教育者尽快成为人才,于是学校在市场的导向和人们需求的吸引下热衷于搞专业化、技术化的速成教育,这也是一种满足“社会需要”的教育。不过此时的“社会教育”已从先前的为极权统治者培养奴隶变成了为金钱培养奴隶罢了。毋宁说都不是潘光旦所说的培养“健全的、完整的人”的教育。
究竟怎样才是“人”的教育让受教育者学会区分是非真伪,使这种辨别力不仅仅限于科学家、哲学家;学会辨别善恶荣辱,使这种辨别力不限于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会识别利害取舍的途径,使这种辨别力不限于商人和企业家;学会美丑精粗的鉴赏的能力,使这种审美能力不限于文学家、艺术家。人由“自求”至“自得”,便是水到渠成。
怎样才是人的教育?这个问题几乎贯穿在潘光旦的所有著述中,下面让我们看看潘光旦都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潘光旦认为人的教育是“自由的教育”,以“自我”为对象。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教师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潘光旦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培养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是“自由教育”的精义,只有这样,教育才能真正进入“自我”状态。所谓“自求”至“自得”,便是水到渠成了,“自我”便达到了教育的目的――成为“自由的人”。也就是前边谈到的“至善”境界里的健全的、完整的人。潘光旦用先秦的一句老话概括了这种“自由的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他进一步解释:“明”就是西洋人所说的“认识你自己”;“强”就是战胜自己,能控制自己欲望情绪。一个人认识了整个世界,全部历史,而不能认识自己,这个人终究是一个愚人。一个人征服了世界,征服了全人群,而不能约束自己的喜怒爱憎,私情物欲,这个人终究是一个弱者,弱者与愚人怎配得上自由?实际上自知(认识你自己)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而是贯穿在受教育者的全部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教人认识自己,尤其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潘光旦所说的“能力上的限制”,不是指技能说的,而是指人的天性局限,黎鸣先生对这种“局限”有过很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在一切人身上都存在着一种先天本能,即人性原恶,主要特点是任性、懒惰、嫉妒,这是人皆有之的原始精神病态,是一种天生的人性局限(见《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潘光旦提出的教育应该教人认识自己,就是认识到这种“局限”,从而培养起克服这种“局限”的能力(意志力、毅力),少受些成见的蒙蔽,实质上就是启蒙教育。因为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成见”太多,蒙蔽了人们的思想,约束了人们的精神,使人的个性受到极大的戕害,人只有从这种“成见的蒙蔽”中挣脱出来,才能走向成熟,才能拥有理智,才能真正有了自知之明。自胜(战胜自己)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长期的磨练,这种磨练尤其体现在日常的一些小事情上,就像高尔基所说的“哪怕是对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克制,也会使人变得强而有力”,在克服人性原恶(任性、懒惰、嫉妒)、改变这种先天性局限中,诚如黎鸣先生在《人性报告》中说的,既要靠外部力量,更要靠内在人性的精神力量。所谓外在力量,即客观上的压力:由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间出现的压迫、饥饿、寒冷、疾病、死亡……所谓内在精神力量,即指人的自我控制力,那种在各种欲望的躁动中能够自我约束、控制住自己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先天具有的,是后天习得的,特别是在青年期教育中通过不断地战胜自己培养起来的。由此看来,教育就是教人“认识自己”与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对“自我”的培养。潘光旦之所以批判近代中国教育的专业技术化倾向,是因为原本以“自我”(学生)为主体的教育变成了教师为主体,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训练(灌输与考试),教师的功用仅是实用意义上的教学而不是教育,学生的“认识自己”大都是通过考试成绩实现的,显而易见,这种“认识自己”是极其片面有限的,所谓人的全面培养也就无从谈起了。潘光旦认为中国近代教育中的德、智、体划分是十分牵强的,不能涵盖“健全的、完整的人”的全部内容,在教授方式上绝对划分也是不可能的。他在考察欧美教育时发现西方社会的教育旨趣有这样六个方面:关于健康的、关于财富的、关于道德和宗教的、关于美的欣赏的、关于智识的探求的、关于政治和人我交际的,潘光旦将其归纳为德、智、体、群、美、富。这“六育”中,群、富先前教育中未曾提及过,潘光旦个别作了这样的解释:群育就是培养协作精神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所谓富育就是培养吃饭能力、并在生计上富裕的能力。这样的“面面俱到”看上去是很全面的,足以完成“健全的、完整的人”的教育,然而潘光旦认为事实上没有见过从事教育的人采取这样多边形的教育方式,事实上恐怕也无从采取,也是办不到的。这六个方面在教育上是整体,是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实践中对任何一方面施教,都不是孤立地、单一地进行,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其他方面。潘光旦特别指出,除非教学内容与教的方法根本有了错误,否则不会有任何单方面纯粹意义上的教学。正是缘于这个原因,才要求教师不应该是专家,而应该是通才。
批评教育部门基于上述认识,潘光旦对当时的教育部门(1939年)在学校里设立训导处给予了严厉批判:近代教育把所谓训育从教育中间划分出来,根本就是一个错误,是失败的一个招认。潘光旦认为教育的对象就是人生,教育就是人生,学习与做学问的目的都是做人,学问不能离开生活而独立,如今把训育从教育里划分出来,使训育与教育成为并立对待的东西,其结果于受教者是有害无益的。潘光旦进一步解释,人的心理活动至少有三方面:意志、情感、理智,有效的教育就是使这三方面共同协调地发展,所谓训导的意义也都在其中了。将教育与训导划分出来的教育只会灌输知识,开发理智,其他如意志、情感诸方面是无法可施的,这样,一个人的品性是不平衡的,教育的结果不会是一个健全的完整的人。
鉴于“人的教育”是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单独施教的统一体,是价值意识教育的整体,因此,潘光旦特别看重教师的言传身教,看重教师的表率作用。他提出要慎择师资,选择教师不仅要看他的学识多少,学问深浅,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识对他个人的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多少良好的影响,所谓学识与个人操守之间是否是贯通的,也就是教师在言语举止、工作作风上表现出的气质风度。
这种与人的学养贯通的气质风度,对学生尤具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具偶像的魅力,人在青年期都有崇拜偶像的天性,因此教师的深厚的学养与严谨操守相贯通的气质风度是教师必须具备的资质。潘光旦认为教师风度的表率作用远远胜过训导中实行的那些生活戒条和所订的几种奖惩功过的条例。因此,当“素质教育”成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界的主流说法时,且莫忘记提高教师的素养才是“素质教育”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教育只能产生并光大于教育对象生存的土壤
教育只能产生并发扬光大于教育对象生存的土壤。欧美教育的土壤,是欧美的历史背景,欧美的文化传统,欧美的风土人情,即欧美的实际国情。显而易见,中国的国情与欧美是迥然不同的。
今日一些年轻人到欧美转了一圈回来,便大谈“素质教育在美国”、“素质教育在西方”,与中国国情实际又能怎样?关于这个问题,潘光旦在1932年写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甚盼中国教育与欧美宣告独立,而新教育的领袖,应根据中国的需要,在中国国内养成之”,“新教育应当因地制宜”。潘光旦“盼中国教育与欧美宣告独立”,是因为教育只能产生并发扬光大于教育对象生存的土壤。
最后想特别指出的是,学习潘光旦的教育思想,在感叹其博大精深之余,更敬仰他的那种为提高中国人的智识水平,为提升中华民族的审美情操,为富国强民而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诚如他的及门弟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先生用了毕生之力,不顾身体上的和社会上的种种常人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劫难,坚持学习各项先进的学科,去认识人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人的社会行为和规范,以及对人处世的法制和伦理道德,力图为人类寻求一条u2018中和位育、遂生乐业之道u2019。”今日的中国教育界谁能想到,向中国教育、向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并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道德情操彪炳史册的潘光旦先生竟是一位历尽苦难、身患残疾的人?面对这样高山景行的先辈贤哲,能不肃然起敬、能不赫然地深省自问:我们应该怎样继续潘先生曾经献身的教育事业?
人格和境界《费孝通谈潘光旦先生的人格和境界》,全文如下:
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作为学生,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费孝通先生这么讲,既是感性的描述,也是理性的分析。作为面向未来的学者,我们自己的确需要经常反思一下自己,问一问自己对自己是否做过深刻的反省,是否能够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做学问的学者。
如果一个人停留在怨天尤人的境地,缺乏作为战士的奉献精神,那么这样的人是不能成为真学者的。换一种说法,这种人是逃不脱真学者的眼睛的。
思想贡献
教育界知道潘光旦的不多,了解其教育思想的人就更加少了。潘光旦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群星璀璨、名人济济的行列中,以其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问和卓然不群的独到见识成为一位光彩照人的学界泰斗。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我国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那代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行结合的最早成功的范例。潘光旦一生都在力倡的通才教育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当我们走过了近50年的专业化教育的弯路,且痛感这一弯路带来的国民人文素质衰退的时候,重提潘光旦,重温一下这位集科学家的睿智和文学家的文采于一身的教育家的思想,重新认识一下他“发挥了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力图为人类寻求一条中和位育、遂生乐业之道”(费孝通语)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对正在呼唤通才教育和人文关怀的当代中国教育界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