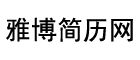欧阳儒秋的个人简介
欧阳儒秋(1918―2007),安徽萧县人,著名表演艺术家、电影教育家。从事表演创作工作七十年,在大量舞台剧、电影、电视剧中扮演了各种角色。其中在影片《创业》中扮演周母、在影片《樱》、《月亮湾的笑声》中饰演性格各异的老年妇女形象,特别在电影《巴山夜雨》中扮演深情、刚强的子弟兵母亲,因而获得1981年首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
人物简介
欧阳儒秋(1918―2007),著名表演艺术家、电影教育家、电影演员、译制片导演。从事表演创作工作七十年,在大量舞台剧、电影、电视剧中扮演了各种角色。
人物生平
欧阳儒秋,原名欧阳如秋,1918年10月生,安徽萧县人,中共党员。早年曾先后就读于徐州少华街小学、徐州女子师范学校、上海大厦大学附属中学、苏州振华女子学校。
1937年在徐州高中肄业参加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学生军女生大队。
1938年转入第五战区青年军艺术组(亦称抗敌剧社),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戏剧运动,演出话剧《钢表》、《壮丁》、《八百壮士》等抗日戏剧。9月参加抗敌演剧队第二队任演员,演出过《闹元宵》、《挖公路》等话剧。这一年,在鸡公山与与时任第五战区青年团艺术组教员的沙蒙相识,以后成婚。长沙大火时,演剧二队从长沙撤退,上面要求队员集体加入国民党,沙蒙夫妇不愿加入,断然离开演剧队。
1939年,沙蒙、欧阳儒秋同到重庆北碚陶行之主办的育才学校任教。
1940年,在重庆与周恩来结识。“皖南事变”后,欧阳儒秋伪装为新四军家属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刘钟濉先期到达延安,沙蒙则在重庆由上级安排转去香
港。
1941年赴延安参加戏剧、新秧歌运动,任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演员,演出《夫妻识字》、《跑旱船》、《栽树》、《打花鼓》、《血泪仇》等秧歌剧。
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东北文工团一团演员,离开延安赴东北沈阳,任演员、教员。演出话剧《日出》(饰翠喜)、《把眼光放远点》、《粮食》等剧目。导演过话剧《谁劳动是谁的》、秧歌剧《全家光荣》和《井台记》等。
1945至1948年在东北文工一团,从事戏剧导、表演创作与教学工作。
1948年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了电影表演和译制片导演工作。参加拍摄《光芒万丈》、《赵一曼》、《葡萄熟了的时候》等影片;并导演苏联译制片《被开垦的处女地》、《顿巴斯矿工》、《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
1948至1954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原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及译制片导演。
1955年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1956成立北京电影学院,即从长春调至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在表演系从事教学工作曾先后参加表55干修班、表56班、表57班、表60乙班、表62甲班、导64班、表78师资班、表83成都短训班的教学工作。先后任表演教研组副组长、表演系领导小组组长、院领导小组成员、表演系副教授。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重建,任学院领导小组成员,全面主持表演系工作。其间导演过《烈火红心》、《北大荒人》、《青春之歌》等话剧;先后拍摄过《大木匠》、《创业》、《樱》、《巴山夜雨》、《月亮湾的笑声》、《家务清官》、《我、你、他》、《明天回答你》、《孔府秘事》、《天地人心》等影片。
1978至1980年任学院领导小组成员,全面主持表演系工作。
1984年离休。
2007年12月27日因病去世,享年89岁。
艺术特色
她的表演,以深沉、含蓄、质朴见长,所塑造的《樱》中的母亲形象,被日本友人誉为“大地式母亲形象”、“典型的东方母亲形象”。此外,还拍摄过《雪花静静地飘》、《金牛》、《母爱》等电视剧。
主要作品
1949:《光芒万丈》(东影)饰周妻。
1952:《葡萄熟了的时候》(东影)饰周大娘。1950:《赵一曼》(东影)饰吕大娘。
1957:《大木匠》(北电实验厂)饰桃叶妈。
1974:《创业》(长影)饰周大娘。
1979:《樱》(青年厂)饰陈嫂。
1980:《巴山夜雨》(上影)饰老大娘。《咫尺天涯》(北影)饰 陈嫂
1981:《月亮湾的笑声》(上影)饰兰花妈;《明天回答你》(长影)饰婆婆。
1982:《心泉》(广西厂)饰奶奶;《我,你,他》(青年厂)饰秦旭兰;《家务清官》(长影)饰岳母。
1984:《月亮湾的风波》(上影)饰兰花妈;《孔府秘事》(北京科影)饰张姥姥。
1991:《苦乐三兄弟》(长影)饰肖桦老人。
1994:《天地人心》(长影)饰李大娘。
获奖记录
因在《巴山夜雨》中扮演深情、刚强的子弟兵母亲,1981年获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并获第二届文汇电影奖最佳女配角奖。
1993年荣获第四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
丈夫简介
沙蒙与欧阳儒秋是著名的影坛夫妇。
沙蒙(1907--1964)著名电影艺术家。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团体,抗战后期到延安,任鲁艺戏剧系教员兼实验剧团团长;解放战争时任东北文艺工作一团团长,后长期在长影、北影从事导演工作,代表作是影片《上甘岭》。
人物关系
合作最多的男演员仲星火 Xinghuo Zhong(演员)
合作作品(3):
《巴山夜雨》、 《月亮湾的风波》、 《月亮湾的笑声》
合作两次以上的影人TOP10许还山 Huanshan Xu(演员)
合作作品(2):
《咫尺天涯》、 《樱》
张雁 Yan Zhang(演员)
合作作品(2):
《月亮湾的风波》、 《月亮湾的笑声》
韩小磊 Xiaolei Han(导演)
合作作品(2):
《咫尺天涯》、 《樱》
方义华 Wenhua Fang(编剧)
合作作品(2):
《月亮湾的风波》、 《月亮湾的笑声》
江韵辉 Yunhui Jiang(演员)
合作作品(2):
《樱》、 《咫尺天涯》
程晓英 Xiaoying Cheng(演员)
合作作品(2):
《樱》、 《咫尺天涯》
张珥 Er Zhang(摄影)
合作作品(2):
《月亮湾的笑声》、 《月亮湾的风波》
詹相持 Xiangchi Zhan(导演/编剧)
合作作品(2):
《樱》、 《咫尺天涯》
曹作宾 Zuobin Cao(摄影)
合作作品(2):
《樱》、 《咫尺天涯》
刘俊生 Junsheng Liu(演员)
合作作品(2):
《明天回答你》、 《孔府秘事》
人物访谈
请问您是怎样走上艺术道路的?
欧阳儒秋:其实,在13岁以前,我只是江苏萧县的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我的生活就是上学读书,偶尔也看看电影,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和表演,会和艺术发生什么关系。直到进入中学,学校的一些文艺节目已经包括了话剧和歌舞等等多种形式,很多同学演出《葡萄仙子》、《小小画家》,而那时候的我却只是个观众,没有上过台,也没有想过上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许多青年学生去南京进行请愿。我是跟着年龄更大一点的学生坐火车去的,队伍一旦步行,就要赶不上,只能是人家走路自己跑步。和同学们到达的时候,南京总统府已经聚集了来自北大、燕大等许多学校的爱国学生,我们也加入了这支队伍。蒋介石终于露面了,然而只是敷衍了几句话之后就立即消失了。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个情形,简直好像是总统“钻”了回去。而总统府前的学生,却久久没有散去。影,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和表演,会和艺术发生什么关系。直到进入中学,学校的一些文艺节目已经包括了话剧和歌舞等等多种形式,很多同学演出《葡萄仙子》、《小小画家》,而那时候的我却只是个观众,没有上过台,也没有想过上台。
从南京回来之后,学校也成立了救亡的团体,排练宣传抗日的各种节目,为学生和群众举行公开演出。当时是意识不到什么危险的,因为我还只是一个初二的孩子。然而后来,那次参加请愿的三年级学生全部被更高一层的学校拒绝录取,其余低年级的教室,也开了一道窄窄的口子,用来监视。过了没几天,为了禁止学生的集体活动,学校给我们提前放了寒假。
虽然如此,各县的学生都成立了抗日救亡的组织,我回到了故乡萧县,到农村去为群众演出。那时候的节目几乎都是《醒狮舞》等宣扬奋起抗敌的节目。青年学生们希望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唤醒民众,保卫中国。从大学到中学,从北京到各地,许多宣扬抗战的题材被搬上舞台。我们几个女同学就说,男生都排了节目了,就女生还没有,我们就想演一场小话剧。由于没有经验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最后选择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来排练,因为这个戏既有爱国主义的意义,又只需要两个演员。
问:既然没有演出经验,那排练怎么进行啊?
欧阳儒秋:当时没有导演,而且也不知道“导演”是什么。我们演戏的两个人从来没听说过“演技”为何物。就这样,两个小姑娘硬生生找人来教了几句普通话,把郭老的台词给背了下来,上了台,居然还得了个满堂彩。这还是我的表演处女作,当时我演那个弟弟,几乎对艺术一无所知,连在台上吹的笛子,还是同学在幕后“配音”的。
问:在演完《棠棣之花》后,您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已经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欧阳儒秋:也没有。当时我们曾经把红极一时的电影《姊妹花》改编成话剧,也曾经把太极拳作为节目来表演。其实,我从来没想过当演员,当时演戏,只是为了抗日。
初中毕业后,我到上海念了高中,并且开始学习普通话。1938年,抗日形势更加严峻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学校,也离开了江南故乡,参加了抗敌演剧队第二队任演员,从此正式加入了革命和艺术的洪流,并走上了这一生执着跋涉的道路。
问:那您能不能谈谈抗敌演剧队的情况和经历?
欧阳儒秋:当时,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国共实行了合作抗日。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先生当时都在重庆负责政治和文化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成立了各个战区的抗敌演剧队。我想,抗日是最重要的,也想加入,后来通过考试加入进来,成为了一名军人,并且立即随队伍奔赴河南潢川,还有全国各地,进行宣传活动。演剧队的成员包括了水华等后来影响了中国电影史的许多重要人物。我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学习一些表演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问:当时的条件一定很困难吧?
欧阳儒秋:我们都是无所谓的。什么都不想,反正有利于抗战,叫去哪儿,就去哪儿。几乎是有什么就演什么,只要能够向战士和群众宣传抗日,条件的艰苦和形势的危险全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有时候到了一个村庄,就用门板搭台。女兵们剪了短短的头发,演出需要长发的时候,就地取材做个头套立即就演。而我大多数时候还是在演男孩。当时的群众热烈地欢迎我们,于是我们也马不停蹄地到处演出。
从重庆到延安
问:那么您后来是怎样去的延安?
欧阳儒秋:皖南事变之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大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开始陆续转移。我是和一些战友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前往延安的。在此之前,就经常听别的战友说,延安的气氛才是最革命的,那里的女同志,可不像我们那么“娇气”。(笑)再加上当时的延安已经成了领导抗日的中坚力量,于是,对延安的向往与日俱增。去重庆,最终就是为了去延安的。
问:从重庆到延安的漫漫路程,是不是也充满了艰辛?
欧阳儒秋:是坐着卡车完成的。当时,我的大儿子已经出世,只有四个月。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阻拦,大家都转变成“家属”的身份,而卡车的“使命”是运输药品。大卡车上装满了货物,人只能坐在货物上面。平时车上的栏杆比人高,而那时候,栏杆的顶端却在人的脚底下。道路崎岖,卡车颠簸得很厉害,只有紧紧地抓住它,才能避免掉下来。临走前,我带了一大包的尿布,晚上休息的时候,就赶紧给孩子洗尿布,由于太疲劳了,尿布在火上烤着,人却在打盹,一不小心就烤糊了;要不然就是挂在车栏杆上晒着,车在行进中,尿布被风吹走了――所以到延安后,只剩了十八块,都不够使了。
问:那么苦的条件,怎么能坚持下来?
欧阳儒秋:那个时候,只要能抗日,怎么着都行。”
问:您在延安的生活和工作是怎样的?
欧阳儒秋:到了延安后,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校。组织上安排我进入“鲁艺”学习。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接触了斯坦尼体系以及正规的表演训练。延安当时的环境是很重视思想教育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文艺理论。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等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演出的。我和同志们也积极地响应一些号召,有时候特意去看老乡打腰鼓,也要立即学会打腰鼓,一旦学会了,就要反过来为老乡们表演,还借这个形式宣传革命思想,老乡们非常欢迎。
问:您的工作那么忙,怎么有时间照顾孩子呢?
欧阳儒秋:根本就顾不上他。儿子还太小,可是也没有办法。只要工作起来,孩子一跌倒,就哭着叫“妈妈”,“摔倒了!”我呢,就说:“摔倒了爬起来!”所以时间长了,孩子每次跌倒,先叫“妈妈摔倒了”,然后自己接着说:“摔倒了爬起来。”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孩子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一个月只能见孩子一次面。
延安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文艺工作者也要参加劳动,以保证“自给自足”。我是个特别好强的人,一开始,从小只会读书写字的我,根本不会纺线,别人纺一等线,我纺出来的线却粗细不匀。但是我不服输,而且在我的心里,觉得只要党号召的事情,别人做到了而自己做不到,就不叫革命。所以虽然要同时兼顾学习和演出,晚上我也会点着油灯练习纺线,最后,也纺出了一等线。
1945年,抗战胜利了。更多的更新的工作也要开展了。在田方老师的介绍下,欧阳老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派一部分人员到东北去进行接收工作。文艺工作者也一路开了过去。欧阳老师离开了自己的孩子,离开了延安。留在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是通过像电影《啊,摇篮》中那样的过程和故事,才逃出敌人的炮火的和父母见面的。在与儿子分别的四年之后,也就是1949年,欧阳老师在一次拍戏路过北京的时候,顺路去找自己的孩子。那时候,孩子长到九岁了,可母亲已经不认识儿子,儿子也不认识母亲了。欧阳老师找到当时十一岁的舒晓鸣老师,因为在分别的时候,舒老师的年纪还稍微大一点,在她的帮助下,母子才得以见了一面。
在东北正式接触电影艺术
问:您到东北后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
欧阳儒秋:当时,文艺演出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进行政治宣传,以此来让东北人民了解党,以及各种路线和方针。因此,党的每一个新的革命任务出来,我都要和战友们冲在最前面,是打头阵的。而且,由于节目形式活泼生动,贴近群众,通俗易懂,我们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演完了关于减租减息的节目,农民就说:“你们演完了,轮到我们演了。”就这样,当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便可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这样的宣传工作,我们几乎走遍了东北三省以及当时的热河。因为内战爆发,常常需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有一次,一下子从本溪,经过沈阳,丹东等十几个城市一直转移到了哈尔滨。最后,在兴山,接收了原“满映”的人员和设备,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正式接触电影这门艺术。
问:《赵一曼》就是那个时候拍摄的,对吗?
欧阳儒秋:是的,我在里面扮演一位支持革命的老大娘。
问:在以后的许多影片中,您都是以这种老年女性的形象和观众见面的。这样的角色并不漂亮,您有没有过其他的考虑?
欧阳儒秋:演这样的角色,自己是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甚至都没有想过选择。反正我脑子里只有革命,拍好电影就是干好革命工作,所以无论演什么,都要努力的演好,而不要考虑别的。无论演的是谁,演员要做的就是把人物研究明白,然后再演出来。
问:听说您还做过译制片导演的工作?
欧阳儒秋:在东北的时候,由于我党与苏联的关系,双方的电影交流非常频繁。我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自学俄文。就这样,我执导了《被开垦的处女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一系列的苏联译制片。
问:我很好奇您是怎样完成从演员到译制片导演的角色转变的?
欧阳儒秋:为了工作需要,就去努力地做,“转变”这个词,根本就不存在。
在欧阳老师的话里,能听到的只有“革命”这个词,可以感受到,她对艺术是非常认真的。她至今仍然念念不忘地告诉我:“我这一辈子拍的最差的一部电影就是那时候的,配音演员全是东北腔。”
欧阳老师隐忍、慈祥的母亲形象,凝聚了我们民族精神中最坚韧厚重的部分,正是这样的母亲给了中华儿女力量,从苦难中走向新生。
由于全国形势的不断发展,电影业也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欧阳老师就是在那时起开始担负起培养新成员的任务。还是像当初自己当演员一样,欧阳老师并没有经过什么培训,或者思考,甚至一个转变的过程,革命,就是要随时随地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并且调动一切精力去适应所有的情况。
就这样,欧阳老师在东北工作了十年之久,直到1955年,她调回北京,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一个正直的人,才能做一个好演员
问:您回到北京后就从事电影教育工作吗?
欧阳儒秋:回到北京之后,孩子依然上寄宿学校,我是一心扑在了学习上。在1956年,由于我曾经培养过一些电影新人,有一定的教育经验,所以组织上调我来到新成立的电影学院,担任教学工作。作为新中国电影艺术教育的开拓的一代,我最为重视的,是向学生系统地传授斯坦尼体系。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虽然有中译本,但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只是前半部分被翻译过来,后半部分强调通过戏剧动作去理解和表现角色的内容却没有出版。我只好利用自学的俄语,来翻译这部分,遇到困难,就请以前做过译制片翻译工作的同志来帮助。由于希望把一切所知所学都传授给学生,经常是辛辛苦苦准备了两个星期的东西,两个小时就讲完了。只能花更大的工夫去充实。
问:除了表演理论外,您还重视什么?
欧阳儒秋:那就是学生的思想工作。除了讲斯坦尼,我用大量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在开始教学的时候,我还曾经提倡按照苏联的方式,多多进行小剧场表演,来锻炼学生。然而这个却被批评为“个人英雄主义”。我当时无法理解,可是,我也没有辩解,因为我依然相信,组织和上级就是正确的。直到改革开放后,我曾经提倡过的方法重新使用起来。不过,我也并没有觉得任何的委屈或者不满,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的心中,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演戏,好好带学生。从事教学后,如果哪里有需要,要我去演一个角色,我就立即去演,而平时,则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当中。当时,电影学院的学生要出去实习,不仅拿不到劳务,还要付给单位实习费用。我在拍戏的时候,就会和制片厂协商:片酬我不要了,能不能把这个顶了实习费,来带几个学生参加拍摄。影片《巴山夜雨》拍摄的时候,我就带了两个学生,影片拍摄结束,厂里的人还为我的学生树起了大拇指。
问:您觉得怎样才是具备成为一个好演员的条件?
欧阳儒秋:怎样成为一个好演员?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朱琳是电影学院招收的第一届业余班的学生,她演过一个只有几集的电视剧,叫做《弯弯的石径小路》。我到后来只看自己学生演的戏,所以就专门去看这个戏,看完了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人,我对别人说:“张国立一定能成。”
当时,张国立离成名还远,而且,在那部戏中,他的表演还很稚嫩。
问:我还不是很明白。
欧阳儒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到上海试镜,试了三次才过,旁边的一个女孩子,试了一次就过了,我对那个女孩说:“考电影学院吧。”
那女孩的名字叫崔新琴。
问:那请您总体上总结一下,什么才是做一个好演员的必备条件?
欧阳儒秋:一个正直的人,才能做一个好演员。能当好演员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演技是可以培养的,但重要的是做人。
文化修养也是很重要的。钱学格在当年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曾经差点没有被录取,是我坚持要了他。我说,一个中学各门成绩都是五分的同学,无论如何都得收下。连谢飞老师等等很多学生,当时都是毕业于101中学的,那可是北京的重点学校,从中走出来的,都是文化好思想好的学生。
在我要求欧阳老师给现在的电影学院学生一句忠告的时候,她微笑不语,我替她说了八个字:“好好做人,好好拍戏。”她点点头,说:“就是这样。”
问:文革的时候您也被停止了工作吗?
欧阳儒秋:课不上了。
问:可是当时应该不止只是这样啊?
欧阳儒秋:也就是挨整吧。
欧阳老师就此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欧阳老师的女儿告诉我,那时候学校里乱得很,欧阳老师的一套教学方法,被作为修正主义进行批判,而且由于曾经在鲁艺学习过,因此被当作周扬的跟随者受到批斗,耳膜都被打破了。
可是,我却想象着,她曾经用像现在这样的慈爱和平静的语气,给她的学生讲革命的道理,不是照本宣科的灌输,不是故做姿态的应付,而是真心诚意地去沟通,去表达,去告诉她面前的年轻人,中国电影和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以及走到今天,曾有过怎样的坎坷和风雨。也只有在讲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欧阳老师的脸上第一次浮现一种追忆往事的沧桑,混合着一股特别的甜美,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她曾经在五十五年前就开始的付出和爱,她曾经在五十五年前就对电影学院播下的祝福和希望。
我问欧阳老师:“您觉得从最开始建校,到现在您离开电影学院,我们学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电影学院,现在也没有。”欧阳老师说。
后记:
面对欧阳老师,我依然不得不去问一些类似于“为什么?”、“您当时怎么想的?”之类的问题。欧阳老师的女儿说:“你什么都不要问,只要明白一点:他们就是要革命,所以共产党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其实原来一切就这么简单。那是一个简单的年代,很多重大事件曾经风起云涌,然而创造历史的人在历史进程中想得其实再简单不过。我问欧阳老师最喜欢的影片是什么,她回答说“好的片子”,我问她最喜欢的导演是谁,她告诉我,她和任何一个导演拍戏,都会好好合作,因为那是革命工作。在我小心地提到吴永刚、水华等等大导演的名字时,欧阳老师依然用平静地语气说:“我对所有的导演都没有特别的印象,我就知道要好好演戏。”当我问她对她影响最大的导演是谁的时候,她轻轻地说:“我的丈夫。”
我回头看了看欧阳老师的女儿,她说:“就是沙蒙。”
这是采访的整个过程中欧阳老师唯一的一次提起自己的爱人,他们的爱情和幸福,应该属于那一种我们不可想象的故事。在战火中浴火而生,在和平中历久弥坚。他们像大多数前辈艺术家和革命家一样,是聚少离多的,然而欧阳老师对于这些,只是用“为了工作必须如此”来解释,没有遗憾,没有埋怨。我问欧阳老师:“那么您觉得,沙蒙老师从哪方面影响您呢?”
她想了许久,说:“各个方面,还是党影响最大吧。”
然而我知道,真正相爱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真正的那种“润物细无声”,就因为无法形容,才是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我试图用一种适当地方法去问欧阳老师,在生活中她是个怎样的女人,但是面对她的笑容和白发,我忽然觉得了这个问题的苍白。而欧阳老师还是回答了我,她笑着解释说,她不会做饭,除了为革命演戏,就是为革命教学。她塑造过那么多母亲的形象,然而她没有花太多的时间给自己的子女。她只是会琢磨角色,塑造角色,教会学生,扮演角色。有空的时候,她就会看书,这恐怕算她唯一的爱好。然而这个爱好也不是“业余”的,她提到的第一种书就是“斯坦尼”,她也看戏曲,研究戏曲中的表演,以便在教学和实践中借鉴。我提到看片,欧阳老师说,她以前是好片子都会看,而现在,她只看自己学生演的或者导的片子了。
从欧阳老师家出来的时候,重新走入北京的冬天。但是路边的黄树叶却让我想起了刚刚告别的那个季节,既而想到了欧阳老师的名字:儒秋。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欧阳老师没有讲过大道理,甚至很少提到“我”这个字,她很像秋天――这个季节很美,这个季节具有经历了冬天的准备,春天的萌发,夏天的繁华后达到的那种极致的绚丽。而秋天之所以美,是因为她以最彻底的简单包容了最深邃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