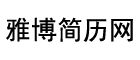刘继明(作家)的个人简介
刘继明,1963年11月17日生于湖北石首,高中毕业后曾回乡务农、随父做生意、学瓦匠,在乡镇和县文化馆工作。1987只身赴新疆漫游。1988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毕业后历任湖北省歌剧团(今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剧,《海南法制报》副刊编辑、《特区法制》杂志总编室主任,《长江文艺》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等职。2007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2012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基本内容
刘继明,1963年11月17日生于湖北石首,高中毕业后曾回乡务农、随父做生意、学瓦匠,在乡镇和县文化馆工作。1987只身赴新疆漫游。1988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毕业后历任湖北省歌剧团(今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剧,《海南法制报》副刊编辑、《特区法制》杂志总编室主任,《长江文艺》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等职。2007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2012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1983年发表诗歌处女作《献给安柯的诗》,1985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双管猎枪》,1992、1993年在《收获》发表中篇小说《蓍草之卜》《浑然不觉》,1994、1995年在《上海文学》和《人民文学》发表《前往黄村》、《海底村庄》、《明天大雪》,《投案者》《我爱麦娘》等“文化关怀”小说,引起文坛注目,被誉为“晚生代”(亦称“新生代”)的代表人物。
2002年,赴中国长江三峡总公司挂职深入生活,创作并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和长篇小说《江河湖》,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
2005年后,以《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乔姆斯基和知识分子的道义承当》《革命、暴力和“仇恨政治学”》《小说与现实》等随笔、文论及《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小学徒》等小说,成为“底层文学”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之一。
2012年至2013年,与诗人郎毛创办《天下》杂志。
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等奖项十余次。
作品曾被译成德文由欧洲大学出版社(Eeropean University Press)出版。?
主要著作
1996年:《我爱麦娘》,小说集,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年:《仿生人》,长篇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柯克或我经历的九桩案件》,长篇小说,群众出版社
2000年:《中国迷宫》,小说集,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年:《太阳照在天鹅洲上》,中国文联出版社“中篇小说经典文库”
2003年:《尴尬之年》,小说集,大众文艺出版社版
2003年:《青少年文学读本》(三册),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一诺千金》,长篇小说,花山文艺出版社版
2003年:《我的激情时代》,思想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
2004年:《梦之坝》,长篇报告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送你一束红花草》,小说集,武汉出版社
2009年:《走向南亚》,长篇报告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江河湖》,长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刘继明诗选》,诗集,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年:《湖北作家文库-刘继明卷》,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年:《我爱麦娘》,小说集,中国华侨出版社?
主要奖项
1992年:《城市的故事》获湖北省首届戏剧文学剧本奖
1994年:《海底村庄》获上海文学奖
1994年:《作鸟兽散》获长江文艺优秀中篇小说奖
1995年:《柏慧与当下精神境况》(与昌切合作)获山花理论奖
1996年:《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获全国优秀小小说提名奖
2002年:《神皇洲》获长江文艺优秀诗歌奖
2005年:《用作品构筑我们的道德》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2005年:获湖北省文化精品生产突出贡献奖
2006年:《放声歌唱》获长江文艺优秀中篇小说奖
2006年:《梦之坝》获屈原文艺奖
2006年:《梦之坝》获湖北文学奖
2009年:《梦之坝》获徐迟报告文学奖
2010年:《小学徒》获选小说选刊年度短篇小说排行榜
2012年:《江河湖》获湖北文学奖
2012年:《江河湖》获湖北出版政府奖
2013年:《江河湖》获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人物访谈
把思想还给文学―刘继明访谈
■ 写作是一种冒犯,既有艺术上的,也应该包括思想上的
李云雷:在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对当前的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我想这主要是源于他们认为“纯文学”应该与现实无涉,长此以往,也就丧失了这种能力,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或者是“不及物”的个人梦呓,或者是“陈旧的”――关心的仍是二三十年前的问题,构思、倾向或“结论”也是人人都知道的,毫无新意。而在我看来,你是很少的能对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的作家,这可以说是对作家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继明: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从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在我印象中,八十年代的作家们对文学之外的事物都是很关心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市场化的启动,人越来越物质化和原子化,文学也越来越内心化、个人化,作家的视野也就越来越狭窄,谈起形式技巧想象力之类津津乐道,对文学以外的东西却丧失了基本的兴趣和能力。所以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学者和作家对此提出了质疑,比如李陀呼吁反思“纯文学”,韩少功也说“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等等。我大概也属于对这种状况“不满”的写作者之一吧。
李云雷:你的一些思想随笔,如《走近陈映真》、《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回眸五七干校》、《革命、暴力与仇恨政治学》等,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请问这些思想随笔在你整体的创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刘继明:前年我在上海做过一次题为《小说与现实》讲座,其中我谈道:有一段时间,由于个人生活中刚刚遭受了一场灾难,再加上后来一阵子身体又很糟糕,所以心里特别虚无,像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路那样,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那时我差点儿也成了一个基督徒,想给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个依托,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那时我看的书也都是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写作一些思想类的随笔,想自己为自己解开一些疙瘩。经常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之类听上去很幼稚,但又是很根本的问题。我逐渐意识到人仅仅解决了内心的信仰还不够,还得搞清楚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才行,这就得保持一种对此岸世界的热情,所以慢慢地,我又开始把目光转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所以,随笔对我写作的影响自不待言,它们是我文学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李云雷:我觉得对思想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你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有不同于他人的视角,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发现与呈现,比如你的短篇小说《茶叶蛋》、《小学徒》,以及最近的《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请问你如何处理思想与艺术的关系?
刘继明:思想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界对这个问题是一直忽略和刻意回避的。最近几年似乎有人重新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我不赞同有些人将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做抽象化的理解。
首先,给文学赋予精神深度,绝非是一种简单的嫁接,而取决于作家对世界的整体认知能力。这固然需要写作者加强自身的知识素养,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其次,在文学范畴内讨论“思想”,必须将它跟特定的时代和现实境遇联系起来,否则就会陷入形而上学、凌空蹈虚的窠臼。再深刻的思想或者哪怕是真理,如果不与现实发生联系和碰撞,都可能是无效的。而这种情形在当前文坛并不少见,比如有人也呼吁“让思想进入文学的前沿”,可当他们面对真正具有思想锋芒和批判精神的作家作品时却常常视而不见,甚至进行贬损和排斥。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
记得台湾作家张大春说过,写作就是一种冒犯。在我看来,这种冒犯既有艺术上的,也应该包括思想上的,不少人只强调前者,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否认后者,未免隔靴搔痒,而且是对文学存在价值的一种遮蔽。
■ 无论对底层文学,还是整个中国文学,我都不是很乐观
李云雷:6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部分都受到“先锋文学”的强烈影响,但很少有人最终突破这一影响,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而你是一个例外,我认为你的创作有一个“从先锋到底层”的转变轨迹。
刘继明:九十年代以来,我的写作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变化是我自己都始料未及的。究其缘故,除了个人经历,无疑也跟中国社会的剧烈震荡和时代蜕变密切相关。曾经有评论家把我纳入一些文学思潮和流派来讨论,但我也许哪一派都不是,记得1995年,李洁非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我是以先锋派之名行古典主义之实;而在某些大力推崇“晚生代”写作的评论家看来,我对历史和传统的兴趣跟晚生代的“个人化”写作又显得格格不入。我自己觉得,无论对于时代,还是文学而言,我都是一个在边缘游走的人。
我写作上的变化,其实从九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如后来被评论家当做“底层文学”来讨论的《请不要逼我》、《被啤酒淹死的马多》以及《父亲在油菜地里》和《火光冲天》等中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发生这种变化,用一句过时的话说,是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教育了我。
李云雷:我觉得相对于另外一些作家,你对底层生活的表现有一种自觉意识,并且有理论上的思考,我们以前也谈到过“底层文学”有可能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不知你现在对此有什么新的思考?
刘继明:底层文学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它是否能够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我觉得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纯文学”与消费主义盘根错节的时代,要想改变非一时之功。更何况,底层文学本身也充满了各种内在的矛盾和歧义。我上次在清华大学的底层文学讨论会上发言时说过,“当底层文学在美学趣味上越来越符合纯文学口味的同时,其价值立场上的异质性和批判力量被大幅度地削弱,除少数作家的创作外,从整体上变成了一种消弭意识形态裂缝,由抗争走向和解,由批判走向迎合的u2018亚纯文学u2019样本,从而与底层文学的u2018精神父亲u2019越来越没有什么瓜葛了。”这也许可以看做是我对底层文学的一种忧虑。
无论对底层文学,还是整个中国文学,我都不是很乐观。但我还不至于像有人悲观地认为小说应该走进博物馆。因为我相信,文学的发展不是某些主宰话语权的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设计定稿的,它必须接受时代和历史的检验筛选。时间终究会对那种畸形和浅薄的艺术给予有力的矫正。
李云雷:你早年的生活很艰辛,也很复杂,包括到新疆流浪、去海南和朋友创办刊物,以及心爱的人早逝的悲剧等,在你的散文随笔中可以看到你刻骨铭心的情感与回忆,我想这对你的创作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不知你是否愿意谈一谈?
刘继明:写作除了受制于时代,个人经历也在其中发挥着隐秘的作用。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经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履历表上看得见的,还有一种是履历表上看不到的,即精神履历。二者并不一定是重叠的。我觉得,后一种比前一种更重要,它往往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内在品质。
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论悲伤》,谈到“悲伤”对人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悲伤既能让你堕入濒临绝望和毁灭的深渊,也能使你在承受地狱般的折磨之后,获得人生境界上的涅,很大程度上改变你对生命的本质体认,从而使得你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用一种与以前u2018判若两人u2019的态度去审视和俯瞰自身以及周围的人与大千世界。”
李云雷:你的长篇小说《江河湖》刚刚出版,你写了5年之久,不少评论家都给予它颇高的评价。这部小说在取材上与你的报告文学《梦之坝》有相似之处,那么你所要表达的与《梦之坝》有何不同?
刘继明:这个问题,我在《江河湖》“后记”里谈到过。2003年,我在三峡坝区挂职和写作《梦之坝》时,《江河湖》就开始在脑子里萌动了。甚至可以说,《梦之坝》不过是写《江河湖》之前的一种热身和准备。在《梦之坝》中,我关注的是围绕三峡大坝从论证到兴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曲折过程,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政治文化信息。而到写《江河湖》时,我把笔触集中到了人的身上,人与政治、人与历史以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物的活动空间也从三峡拓展和延伸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但对于《江河湖》是否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写作目标,我还持怀疑态度,有待于更大范围以及时间的检验。实际上,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都在同自己的怀疑作斗争。最终之所以坚持下来,与其说是基于写作上的耐心,倒不如说是某种信念支撑的结果。生活需要信念,写作也需要信念。这是我写《江河湖》得到的最大启示和收获。
■ 文学上的“全球化”可能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某种潜在的危险
李云雷:你近年和海外的作家接触较多,包括接受访谈、参加活动,或者出国访问,这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刘继明:就我有限的对外交流经验来看,中国文学正在经历的一切,比如商业化、娱乐化等现象,跟国外的也差不多。全球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文学也一样。中国的主流文坛近年来不断开展各种“走向世界”的推介活动,固然出于组织者急于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迫切心态,但也说明当今中国文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和国际接轨了。但对于这种“接轨”,我还是有些疑虑。
举个例子吧,前不久在武汉和来访的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交流时,觉得在许多问题上我很难苟同,比如他认为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不能算是小说,他认为像巴尔扎克、雨果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早已过时了,这种看法在中国其实很早就有,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个人化、平面化写作以及这些年大行其道的网络写作,就是这种观点的佐证。而维勒贝克的长篇新作《一个岛的可能性》也为他的文学主张做了最好的诠释,我粗粗翻了一下,科幻、玄学、推理、性爱,各种时尚的元素里面应有尽有。这跟当前中国的流行文学如出一辙嘛。
这使我意识到,加强交流和吸收国外的新鲜经验都是必要的,但不能盲目趋同并以此为荣。我觉得,文学上的“全球化”可能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某种潜在的危险――在催生一些拿欧元或美元版税的“国际作家”的同时,更多作家对中国本土问题和现实境遇产生进一步的漠视,从而使中国文学丧失掉自身的传统和经验,变成一种“后殖民文学”。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
李云雷:你关于《都市小说》致湖北作协党组的“公开信”,在文学界与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引发了关于作协管理机制的讨论,我想你当初写此信需要不少勇气。
刘继明:我当初之所以想出来办一份刊物,主要是骨子里的知识分子情结在作祟。现代文学史上,像茅盾、巴金、胡风等人不仅是出色的作家和学者,还办过出版社、杂志和书店。上世纪50年代的赵树理,80年代的王蒙、刘心武,90年代后的汪晖、韩少功等等,也都办过杂志,可以说,作家学者办杂志,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统,也就是你前面谈到的“知识分子传统”。但这个传统现在差不多全被丢掉了。
现在的文学杂志主办者都是职业编辑出身,当然也有办得好的,但大多数人缺少人文理想以及独特或者明确的办刊理念,再加上现行的体制,刊物基本上靠拨款,物质和精神上的驱动力都不够,满足于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甚至把刊物当成了一个利益平台和垄断性资源,从而堵塞了从外部注入新鲜活力的通道。这也是我参加那份刊物招投标受挫的真正原因。当大多数人将办刊物当成牟利工具时,你即便有再真诚的文化理想也是白搭,人家不仅不会理解,甚至没准觉得你也是想“分一杯羹”呢。
同行评价
刘继明的“文化关怀”小说,将浪漫主义的精神与先锋小说的叙述优长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调侃中见悲凉,见悲壮的艺术风格。? ――周介人?
在刘继明的故事中,生活表象已被非理性的盲动所统治。他传达了这种状态,但丝毫也不苟同,反之,他在批判――用理性批判。这种理性与人类多少年来已经形成的对于生命的幸福、完满、健康诸概念是相通的。? ――李洁非?
从总的精神趋向看,刘继明接近张承志一路作家;他不希望救赎他的时代,他只指望奏安魂曲;他是一个颇具存在主义意味的孤独个体,声声呼唤个体自由和美,却无可奈何地将它们送到墓地安葬,静穆地向它们致哀。? ――昌切?
刘继明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具有优越的潜在素质的人物,都处于精神上的流浪和痛苦之中,四处飘泊无处归依,无法找到精神之乡,更无法在现实的生活中寻找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只能在虚幻的世界中实现自己。? ――葛红兵?
刘继明无疑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思想者,他的文章散发着燧石一般的神灵之光,使我们感到古老的思索会成为一种精神体系和脉传,浸润人的灵魂,让我们品味到热闹文学的深处(或者叫角落)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古典气息。使我们听到思想的声音,像无数过去时代的哲人对今天光怪陆离的生活冷静的发言。? ――陈应松?
近年来,刘继明沉入了二十世纪中国错综复杂的大历史之中,致力于重新发现某些被忽略的历史细节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冒险史。《梦之坝》如此,《江河湖》更是如此。? ――雷达
刘继明从一开始就与“底层写作”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不像大多数写底层的作家那样,一味地表达对底层的同情和怜悯,更没有将自己的底层叙述作为底层怨恨的一个宣泄渠道。? ――贺绍俊
刘继明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能力和知识分子气质的当代作家之一。这既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色彩,同时也使他的笔触超越了虚构文本,直接对社会、文化问题发言。刘继明最近的创作为我们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径,这是一条正在延展着伸向前方的路,同时也是一条孤独的路,对这条路探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着未来中国文学的面貌。? ――李云雷